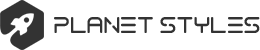父子俩(梅花君子)
父子俩(梅花君子)
父子俩
文:梅花君子 编:一缕清风
一
张浩军感觉前后左右的院子邻居有点臭钱,就不知道咋美,不会让钱下崽儿,把腰包里的钱一股脑全都用在盖房搭屋上。四外邻居们把院墙全换了,换成了红砖到顶的院墙,而且高的很,伸出手都够不到墙顶了。院墙换房子更得换了,本来挺好的四间大瓦房,才盖十多年,就好像过家家似得,来了情绪全都扒掉,一点都不心疼。他心里面不舒服,肺管子里好像揉进了,一大捧细细碎碎的玻璃碴子,鲜血淋淋疼痛难忍。只为垒院墙盖新房,他没少跟儿子打仗。他家现在的房子才盖不到十年,地板砖太阳能卫生间,样样都齐全。院墙才垒十多年,虽然没有高过头顶,却也红砖到顶,水泥勾缝,结实的很,就是再住七八十年也不成问题,干嘛要扒掉重整,那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张浩军吃过饭,还像往常那样,倚在被垛上,抽袋烟好好解解乏。他是个烟鬼,为找抽烟的理由,掏空心计,东拼西凑编了抽烟的歌谣“饭后一袋烟,赛如活神仙,管腿疼管腰酸。”今儿这袋烟,他没抽舒坦。儿子张青用牙签剔着牙里面的残余食物,响亮的打了一个饱嗝,跟他这个当家人对话:“爸,咱家在年内也得扒院墙扒房子,也盖大房子,也垒高院墙。”他听了儿子生不愣的话,一肚子的火。心里面责怪张青,你个混球自己家啥样还不清楚。一扒一盖,来回一折腾,那得造多少钱,他大声说:“你刚才说得啥话,你再给我好好重复一遍。”张青心眼子直,不会拐弯抹角,粗声粗气说:“爸,秀梅跟我说,非得等咱家盖上好房子垒上新院墙,才能跟我结婚。”他急了,恨不得把张青活啦啦吃了:“你他妈的说得倒轻松,盖房子垒院墙,掰着手指头好好算算,得花多少钱。你也不能尽听没过门媳妇的。”张青假装特别委屈,心里面在吧啦吧啦打小算盘。爹心花,很多人都说他跟王二媳妇背地里勾搭连环,男女在一起,尤其是岁数大的男女在一起,那有啥真爱真感情,都得靠钱财维系这龌蹉的关系,时间长了家里的那些钱不都得神不知鬼不觉让亲爹鼓捣进王二媳妇的腰包。他必须得趁着结婚这个机会,把爹手里的存项好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不留的全部挤出来。
张浩军老了,头发都白了一大半,努力控制着脾气,尽力压着火。他现在有很多毛病,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而这些毛病最怕生气上火。十多年前,他在家里发火斗气,不当吃棵小辣葱。有时候他吃着饭跟老婆犯话,霸气的把吃饭的蓝边大碗,毫不吝啬的扔下去,好端端的饭碗,便碎成一片。不到一袋烟功夫,又跟老婆嬉皮笑脸。现在老了,百病缠身,稍微一动气,就心慌气短浑身打哆嗦,就怕急火攻心,彻底玩完。他努力控制着情绪,该不发火时就不发火,慢条斯理说:“我不知道你们年轻人是咋想的,咱这房子这院墙,咋就那么破的。想当初,我跟你妈结婚的时候,就压两间小偏厦子,照样过得有滋有味,在那小厦子里,照样生了你姐和你,日子过得很舒坦。”张青心里明白的好像一泓清清亮亮的水,父子爷们咋滴,在钱财上更得闹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等到爹百年之后,家里的一切都归他。俗话说得好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涉及他婚后的幸福生活质量上,钱财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所以他对爹钱财上不轨行为更得多加防范。他看到老父亲白发苍苍的样子,心里面也不好受,他低着头不敢高声语:“爸,我也不想拆墙盖房的胡作。人家秀梅不干,要死要活的折腾,假如她一急眼,彻底跟我白白了。我再说媳妇那就是难上加难了。”张浩军觉得张青嘴里句句都说的是大实话,不藏不瞒的大实话,假如真要在拆墙盖房上打了铧子,秀梅一怒退了亲,张青很难再说上媳妇,现在女少男多,比例失衡,说一个媳妇,比上天摘一个星星都难,他打了光棍断了香烟,那是这个当父亲的最大的罪过。张浩军不再跟儿子继续死磕,郑重其事的坐起来,烟袋锅敲打着炕沿,把烟袋锅里面的烟灰投出之后,放在烟笸箩里,两只疲倦的眼睛,无精打采的盯着张青,长长地叹了口气:“咱家的情况你应该清楚,存折上还有十多万,圈里还有五头肉牛,刨除这些东西,咱们还能折卖啥。咱总不能把你爷爷老院子卖了吧,总不能把我当驴杀了卖钱吧。”这话说得到家,听起来特别阴损,彻头彻尾的泼皮无赖。我的那个亲爹呀,你咋那么的狡猾,死猪不怕开水烫,为了守住腰包里的那点钱,就可以没脸没皮抵赖顽抗到底。
张青最头疼的就是爸爸装怂,是呀是呀家里面没啥值钱的东西,他闭着眼一掐算就一清二楚,不会那么容易被忽悠。他小时候在二爷爷家常常把玩一个缺了嘴的茶壶,都以为值不了几个钱,被爸爸用两把旱烟换到手,五年后他一转手就卖四千多。张浩军在前后院也是一个非常了得的人物,跟着人先后去过承德、朝阳挖过古墓,倒腾过袁大头,贩卖过老物儿。前些日子,搞萤石矿的鲍老板还开车请他去帮着他鉴宝。他说家里没钱,那是纯粹是扯犊子,上坟烧报纸在忽悠鬼。他想到可这里,眨巴着眼睛,不软不硬的说:“爸,我清楚咱家没钱,穷得眼净毛光,就连耗子到咱家,都没发现啥好东西,一个个都擦着眼泪走。我暂时不结婚了,等啥时有钱,能拆墙盖房,我再找秀梅商量结婚的事。”没想到张青这家伙儿,居然跟他亲爹玩鹰,父子俩互不相让,一来一往展开了拉锯战。
张浩军精神彻底被张青击垮,知父摸如子家里有啥值钱的,存折上有多少钱,他是掌握的一清二楚,趁着这机会穷追不舍,通过各种手段斩断爹与王二媳妇的关系,免得把家里的钱财全部都贴给王二媳妇。他长长的除了口气,没有了刚才的霸气,就好像一只被尖锐的玻璃碴子扎破的自行车胎,瞬间就把那股精气神全部泄露。他那神情多么像一条蹦到合眼上的鱼,耗尽生命能量,鼓腮瞪眼无力的喘着气。张浩军用手指头,反复掐脑门,凡是遇到着急上火的事,就习惯用手指头掐脑门:“我的小祖宗呀,你这些年糟践我多少钱。你学开车那年,一年不到头我就给你花小三万。你跟前院大军在镇里合伙开饭店,我一把就给你七万。这些钱,都打水皮不响。你妈闹病要命的病缠人的病,你不是不知道,从住院到埋葬,整整花了我十五万。你爹就是一个靠种地为生的庄稼人,你就是把我整死,搓成骨头碴子买了,那也不顶用了。”他不能打肿脸充胖子,手里必须得有点养老钱。现在,傻呵呵把钱一个子不留的全都拿出来,以后有个毛病谁管。手中有钱,心里不慌吗?
张青看到爸爸哭唧唧的熊样,心里就好像被纳鞋底的锥子重重的扎一下。他毕竟是我爹,我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挣钱不给我花,还能给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花吗?假如现在,真要是不懂事,不依不饶的逼迫他,把藏在牙缝里的养老钱,全都拿出来,极不情愿的拿出来,那就等于把爹的血全部放干,父子俩的关系,彻底完蛋,你坏了他的好事,父子相向,同室操戈,厮打得头破血流,岂不让人耻笑。
张青缓和了语气,从裤兜里摸出一盒玉溪烟,恭敬的递到爸爸手里,擦着火柴点烟。他笑了,非常柔和的笑,这一点还真秉承了爸爸的良好的基因。张浩军脾气不好,不是一般的不好,太不好了。说着说话,不知那句话呛了他气管,那火气就来了,举起巴掌就打,打完后一掉屁股就烟消云散。前后院的邻居,都叫他“酸脸狗”。张浩军抽着烟,凝结在脸上的懊恼,随着飘出的烟雾,慢慢的消退。他爱烟如命,在他大发雷霆的时候,只要你给他点一支烟,马上就得到缓和。张青呲着牙笑了,满怀心事,不情愿的那种虚伪的笑:“爸,你也别着急上火。明天我借着赶集的由子,到秀梅家走走,嘴里抹着蜜,做做我丈母娘的工作,但愿她能开窍,饶了咱们这一遭。”张浩军被烟呛了肺管,咔咔咳,他攥着拳头轻轻的拍打张浩军的后脊梁,许久才缓过神来:“你呀,就是太老实,一丁点都不随我。你做你老丈母娘工作,那能做通吗?你把秀梅鼓捣大肚了,他们家都上赶门找你。”这番话,把张青臊得满脸通红,急头白脸地说:“爸爸,你这是啥话,咋不教我学好。秀梅可是正经人,我听了你的蛊惑,一时兴起,对她下手,她万一急眼,认为我不是好人,撕破面皮,那不是鸡飞蛋打人财两空吗?”张青的话说得钢镚硬正,心里也藏满了鬼八卦。你不是不肯吐骨头吗,如果把这桩婚事整散了,你这个老头子可就是千古罪人呀。张家的香烟在就此断了,我看你将来百年之后有何面目拜见列祖列宗。
张浩军急了,气不打一处来,摊上一个窝窝囊囊的怂儿子,真是上辈子缺德呀,这辈子遭到报应。他脑门的青筋都鼓了起来,好像一条正在蠕动的蚯蚓,显得特别可怕。他提高嗓门跟儿子进行较量:“你咋就那么不懂事呀,还想把你老爸爸逼死呀。你呀咋就那么软,就是你跟秀梅结婚以后,就是这三脚踹不出一个响屁的熊样,也会受一辈子窝囊气。你就不能学学我年轻时那样子,在你姥爷家我说一不二。你可倒好,连我一个指甲都赶不上。”他企图用激将法,唤起张青的斗志,与他老丈人斗智斗勇,三下五除二把婚结了,彻底完成一个当爸爸的责任,没啥事看蚂蚁上树那该多好呀。
二
张青确实软的很,尤其在爸爸面前,软得好像一个面条。为啥要这样软,那是他个人的私密,不可能与外人明说。他对自己的爹,太了解了,一撅尾巴拉几个粪蛋,都清楚的很。以前,外人都说他爹跟河东村的王二媳妇有一腿,他还曾跟人急过眼,为维护爹的光辉形象,居然在酒桌上吵吵起来,他照着下舌的唐三胖子的脑瓜子狠狠就是一啤酒瓶子,当时就把他打得头破血流,都是一个村的,在众人的说和下,他掏2000元了事。他长了个心眼,悄悄地留意爹的行踪。去年夏天,爹坐公汽去城里,他骑着摩托车尾随,果真跟王二媳妇黏在一起,两个人逛商场,爹给她买了一双凉皮鞋,中午还在北来顺饺子馆吃了饺子,爹要了一瓶小牛二,一顿饭磨磨唧唧吃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然后三拐两拐,去了米家胡同的一个门面房……这事他跟大姐说过,姐长叹一口气,无可奈何说:“这是家丑,就是憋屈死,都不能往外嚷嚷。我看最好的办法,就是想法把他手里的哪些钱,想方设法都扣出来。手头没钱,王二媳妇肯定不跟他好。”张青挠挠脑袋,感觉这倒是好办法,为了让爹早日改邪归正,便拉屎攥拳头暗使劲儿。
张浩军觉得张青就是一脚踹不出一个响屁的熊包蛋,跟这样没囊没气的人生气犯不上,儿子是自己的无论如何得给他娶妻生子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他琢磨好几天,硬着头皮到南山根老亲家那里走动走动。说一句实在话,张浩军跟老亲家甄景明那可是老伙计,当年在一起给建筑队当小工,手里有俩臭钱,在一起没少扯毛蛋,到歌厅唱歌,憋得受不了的时候,还一起找过小姐。他觉得就凭这杠杠的关系,他跟老伙计进行交涉,说点冒尿离谱的话,料甄景荣也不敢跟他翻脸。他坏坏地笑了,假如他真翻脸了,当着亲家婆的面,把当年他们在一起扯毛蛋的丑事,全都说出来,看看谁他妈的下不来台。
张浩军知道甄景明这家伙嗜酒如命,见着酒都比见着亲爹都近便。他便投其所好,骑着摩托车到三泉烧锅打了十斤60°纯粮酒,另外还将压箱底的山庄老酒拎上两瓶,一溜烟就到了甄景荣家,因为提前打了电话,老两口早就在家恭候多时了。甄景荣还真把他当成一盘菜,从柜子里找出一包,精包装的龙井茶,毫不吝啬的全都放进大号搪瓷缸里,端起烧好的水壶,热气腾腾的开水,哗哗的倒进搪瓷缸里,盖上盖子焖。两个人盘腿坐在炕上脸对脸面对面,显得格外的亲热。他们俩都是庄稼人出身,自然都说一些庄稼话。今年种多少亩玉米,种多少谷子,苗青啥样等等。茶沏好后,两个人守着搪瓷缸,对饮起来。甄景荣说姓刘的那个包工头,上个月欠民工三千元,死活不给,那人都给他跪下啦,他老婆住院就需要这笔钱,姓刘的那家伙人话不说,他对民工说死了好,死了再说一个,民工急眼了,一砖头就把姓刘的给揍死了。张浩军听了,咧着嘴笑了,该,我看他不是好浪,浪大有灾。张浩军说,农民工撇家舍业挣两个钱容易吗?一个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忒不容易。那点工资才几个钱,老板们都财黑,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就是赖着不给。向这样欠钱不给的缺德老板,就是欠揍。
张浩军和甄景荣说话之间,饭菜就已收拾停当,两个人不用让,便脚蹬脚的喝了起来。这两个人都是大酒罐,喝啤酒都嫌没劲,都喝60°散白酒。甄景荣焖干两缸酒,甄景荣三扯两扯,扯到了正题上,他质问张浩军:“老弟,你们家啥意思,是不是对我们家秀梅有啥意见?”张浩军笑了,他就是为这事来的,还没等他开口,就有憋不住尿的:“我们家没意见,啥意见都没有,只要你们家大人孩子没意见,找个先生查查日子,只要啥都不犯,啥时结我们都没意见。”甄景荣媳妇进屋搭话了:“我们觉得这俩孩子都老大不小了,把婚结了,安安心心过日子。”张浩军听了老两口这番话,被阴云笼罩的心头,阴云全部被风吹散,暖洋洋的阳光普照,佯装皱着眉头,深深的皱纹里藏满了得意的笑容,却假装长长的叹口气:“我的想法是先结婚,院墙房子以后再翻盖。现在有出息的年轻人,谁还在土窝窝里住,都在城里买楼。我的意思就是先结婚,过个一年半载咱们也到城里买楼。”甄景荣一拍大腿,大声说:“对,对,老弟咱们尿到一壶了。咱们就得让孩子们往城里奔,将来有个孩子,在城里上学也方便。咱们这熊地方,有啥好留恋!”张浩军笑了,深深浅浅的褶皱里,都藏不住得意的笑容。
三
张浩军回到家里,一声不响,与往常没有两样,静观张青这兔崽子的反应。他夜里睡不着觉就在反复琢磨,张青这小子这样蔫不唧的折腾白发苍苍的亲爹,恨不得不让喘气,一下子整死,这个小兔崽子真是脑瓜顶上长疖子脚底下流脓坏透气了。他仔细一琢磨,这臭小子这么折腾他那是没有啥道理的,张青是家里唯一的男丁,上没有哥哥,下没有弟弟,家产没分的没争的,他百年之后,家里的一切都是他的,从法律角度上他可是唯一继承人。他越想越来气,辛辛苦苦把你个兔崽子拉扯这么大,咋还成仇人了,你小子不让我好过,我也想法掂对掂对你,也让你吃鸡毛,肺管子刺痒难忍浑身不得劲。你坏我他妈比你更坏。冷静下来,有感觉这样收拾儿子,老婆在九泉之下责怪他太没人性,好吧赖吧,他可毕竟是你亲儿子,哪怕到公安局做DNA鉴定,他也是你张浩军的亲儿子。你给儿子使坏,这事让外人知道,谁都骂你冒傻气。将来呀,你动弹不动那天,你还得指望人家接屎端尿养老送终。
时隔半个月,张浩军低着头用手在烟笸箩里揉旱烟,对张青说:“你给你老丈人打个电话,顺便把你三姑夫叫上,咱们在镇上的联众饭店吃顿饭。你和秀梅订婚眼瞅着都两年多了,不能再拖了,现在这小姑娘心花花,万一那天跟着别人跑了,咱们不是鸟飞蛋打吗?”张青支支吾吾,想说还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他看着儿子那个熊样,恨不得伸手给他两巴掌。可惜我张浩军好强要面子一辈子,没想到摊上这么一个,窝窝囊囊一脚踹不出一个响屁的完蛋家伙。他来气了,提高了嗓门,火帽钻天的日骂他:“你咋就那么完犊子,让你给你老丈人打个电话,看看把你吓死了。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不争气,你一下生的时候,不如把你摁在尿盆子淹死省事。好了,我不用你打电话,我直接打,我哪辈子缺大德了。”张青不分辨,咕噜着眼睛静观事态变化。他在想,我的亲爹呀,看看你究竟跟我老丈人咋交涉。
张浩军心里有底,当着张青的面直接给甄景荣打电话,直接摁免提,趾高气扬,派头十足,要好好教训教训张青这个小兔崽子“老哥,你啥时有时间呀。”电话里传来甄景荣的说话的声音:“老弟,我听你的孩子们的得赶紧办。我有的是时间,随时随地都可以。”张浩军狠狠瞪了张青一眼,言外之意,多大点的事,你老子一个电话就搞定,不服行吗?他继续说道:“老哥呀,咱们就定在这个星期的礼拜日,把媒人叫上,咱们在联众饭店见面,三八两下,咱们就定好了。没事咱们就喝酒,黑天咱们就住店,晚上安排你洗澡加按摩,保准让你浑身舒服自在。”他打完电话,火气渐消,对呆若木鸡的张青说:“你这今天啥活也不用干,琢磨琢磨结婚都需要添置哪些东西。咱不买太高档的,但总得说得过去,不能让外人笑话咱家太完蛋,不蒸馒头咱争口气。”张青变得更软了,好像一团加水加多的面团,咋揉咋是,捏个啥形就是个啥形。
张青感觉人单势孤根本就斗不过,怕再这样下去会影响父子关系,搞得鸡飞狗跳没法收场,但是让张浩军这样胡作下去,怕他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都搭在王二媳妇身上,觉得心疼气不过,万恶淫为首,整出命案,更麻烦了,有辱张家门庭。他思前想后,还是到大姐家好好商量商量,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他把来意说了一遍,大姐和大姐夫,干挠脑袋愣是没啥好主意。他们总不能回去,直接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张浩军不得跟他们急眼,他们可都知道自己的亲爹啥德行,火爆脾气,动手打人,不计后果。谁都怕把事情整大,不好收这个场。大姐跟张青说:“这可是大事,我和你姐夫脑瓜不好使,还真没啥好主意。”大姐夫一眨巴眼,来了心计,对张青说:“我看呀,这事还得直接找你老丈人跟咱爹谈,他们交情深,说高点低点,他也不好意思急眼。”张青挠挠脑袋,别的还真没啥好法,只能如此这般了。
张青真想骑着摩托车到甄家,把藏在肚子里的话,一股脑跟甄景荣说出来,思前想后还是把烂在肚子里,这是家丑岂能告诉外人。假如他在老丈人面前不管不顾,嘴无遮掩,嘚吧嘚吧,全都说出来,万一甄家嫌弃他家门风不好,恼羞成怒,一下子退亲,那可就弄巧成拙,鸡飞蛋打人财两空呀。错过了,秀梅这个店,恐怕真要打一辈子光棍了……可是窝在心里的话,要是不找个人吐出来,如鲠在喉难受的很呀。他神使鬼差给秀梅打了电话,拐弯抹角说出了他爸人老心花,若是在不想个好法子阻拦,指不定哪一天,他爹就会把家产倒腾给王二媳妇。如今,他和秀梅已经登记都有一年多了,铜帮铁底的法定夫妻,有啥事跟亲爱的梅叨咕叨咕,应该是百病不犯。他可上来了实在劲儿,就好像满满的一口袋黄豆,扎口袋嘴的绳突然断裂,哗啦一声挣口袋的黄豆,叽里咕噜全都跑了出来。他盼望着能得到秀梅的夸奖,知我者夫君也。没想到呀,秀梅听完后,哈哈笑都笑岔了气。他懵懂了,不知如何是好?他紧追不舍,要弄明白她为啥那么笑。这个秀梅,是不是有病呀。任凭他怎么追问,秀梅就是不告诉这里面的秘密,最后扔下一句话“我就是不告诉你,憋死你个傻小子。”
礼拜日镇里联众酒店,张青早早就赶过来,找到老同学的哥哥林大厨,专门选招牌菜,贵贱不计较,只要高档大气上档次,还特意在超市买了一件年份原浆,酒啥样暂且不论,那可是央视上榜品牌。十一点二十张浩军才慢条斯理的走进酒店,坐在饭桌前,先用牙签剔着牙齿里面的饭粒、韭菜叶等杂物,顺口吐在地上,然后在用鞋底子来回碾抹。他看着都感觉有些不好意思,老爹呀你可真丢死人了,地板砖被服务员擦得这么干净,都能照得见人影儿,你可倒好一丁点都不珍惜人家的劳动成果,几口脏东西,就把好好的地面弄得脏兮兮的,可真叫人感觉不好意思。大约也就过十多分钟,甄景荣、秀梅和她妈妈(甄景荣媳妇)来了,保媒的李耀祥也笑哈哈的来了。人凑齐,张青站在门口大喊:“服务员起菜。”大概也就是七八分钟,所有的菜全部上齐。张青坐在席口,负责倒水倒酒等等服务性工作。两家人出于对媒人的尊重,便要他在端起酒杯前,要像模像样造个句,美其名曰祝酒词,他是个场面人,假意推脱一番,便端起满满一杯酒,高声大嗓地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晴空万里,阳光普照,花开朵朵,芳香无比。在这个大好的日子里,我们张甄两家老人坐在一起,笑呵呵的把儿女们的结婚的好日子定下来。根据张甄两家的意思,儿女的好日子定在农历五月初八。现在我请在座的各位亲友,共同为孩子们的好事好日子好结果干杯。”两家老人谁也不敢怠慢,满满一杯酒,一下子全干。李耀祥一个个验完酒杯,哈哈一笑,接着再来第二杯,他继续说:“第二杯,也是个喜酒,不是别人的,而是我浩军我大哥的,我不但要给咱侄儿当媒人,更要给老哥当媒人。你跟王二媳妇眉来眼去已经都好几年了。人家王二的丫头说,她在广州那边都买了楼,钱有的是,根本就没把钱看在眼里,只要老母亲老年有一个知冷知热的老伴,她在县城里给老两口开个超市,自给自足,两个人百年之后,把所有家产全都给张家。我说这么多,就是一个事。先把儿女的婚事办了,过年的时候,趁着王二媳妇的闺女回家过年的时候,把老大哥的婚事办了。这杯酒,必须干,谁不干谁是王八蛋。”这杯酒,桌上的人都干了,就连秀梅的酒杯里的可乐也干了。李耀祥酒劲上来了,一连打了三个酒嗝,长长喘了三口气,鼻子尖上都冒汗了,他继续说:“张家甄家,这第三杯酒,那是关乎我个人的利益。我连着给你们管两宗大好事大喜事,你们得给我多大红包。今天在酒桌上,老张大哥必须表示,要不然我到你们家连吃半个月。”张浩军笑了,满脸通红,从怀里掏出一个大大的红包,郑重其事的双手递给他:“兄弟,你为我们爷俩没少跑腿费心,这点小意思兄弟先拿着,多啥我结婚那天,再给你一个双倍的大红包。”张浩军说完,就笑了眉开眼笑,肆无忌惮的大笑。
散席后,张青算完账,准备陪秀梅在服装城买几件衣服。秀梅笑笑拒绝了,他感觉他跟秀梅有些生分,心里面略过一层阴影。他拿出他爹那种追穷寇不要脸的架势,不顾服务员窥探的眼神,紧紧攥住她手,跟她黏在一起,秀梅突然笑了,悄悄问:“你知道王二媳妇是谁吗?”张青根本就不清楚,傻在那好像一根木头,她说:“那是我亲老姑。”张青有啥傻了,呆呆地站在那,半天才缓过神来,王二媳妇跟秀梅是亲姑亲侄女,这不是娘俩嫁爷俩,看看还是我们老张家的人有魅力吧。想到这里,张青笑了,对张浩军这个亲爹,不由自主的竖起来大拇指。
文学风网站欢迎您
http://swf.wyflash.com/swf/2008-6-5/192812247.s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