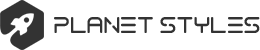命在路途(梅花君子)
命在路途(梅花君子)
命在路途
作者:梅花君子/编辑:叶的奉献
一
曹绍武提着行李被汹涌的人流,磕磕绊绊挤出了候车室,尽管广播喇叭反复叮嘱人们,要注意安全不用拥挤,根本就起不了作用。他头次出这么远的门,觉得有些懵懂,不知所措,被后面的人们推着往前走。他在站台冷清的灯光下显得特别的孤独,嗖嗖的夜风顺着他裤腿钻,连着打两个哆嗦,后悔没多带几件衣服。他把衣服紧紧的裹紧身子,双手紧紧的抱着膀子,跟土里刨食的很多庄稼人一个习惯。他把脖子抻得老长,向着西边张望,前途一片迷茫,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恐慌,那颗心被整得七上八下。
曹绍武渴望马上改变现状,能一把一把的往家里挠钱,攒够钱马上让香兰住院,一刀把那瘤子割掉,根除后患安安心心过日子。他还得挣钱,多多挣钱,长顺一年得了两个奖状,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得供孩子念书。他自己这辈子想念书,大姐二姐三姐四姐死活不让念,怕他考出去老爸没人管,成了他们的累赘。他在镇联中连着两年都考第一,八年级刚念完半年,就被四个姐姐硬是给拽了下来。大姐曹春霞拉着他的手说“老疙瘩,咱爸就你一个儿子,都只靠着你养老。姐妹再多,关键时刻也上不去台面。你呀,就安安分分的好好跟咱爸爸过日子。”他做梦都想考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坐办公室坐小车,天天吃香喝辣,那多么好。一辈子,守着几亩薄田,有啥意思呀。他流泪了,呜呜大哭,繁华锦簇的大好前程,就这样活生生的葬送了。这四个姐姐,咋就眼光那么短呀,要想说服他们,比登天都难........二姐曹春妹用手绢给他擦着眼泪,无限爱怜的说“老兄弟,你别着急。你下庄稼地,哪些庄稼活,你二姐夫三姐夫全都包了。我们都商量了,一家出一千元钱,把房子翻盖了,过一年半载,给你张罗媳妇。”他的命运,他做不了主,被四个姐姐紧紧攥在手里。
曹绍武离开家,就觉得没了根,好像被大风吹拂的枯叶,心里空落落的,一丁点儿底儿都没有,他恨不得马上坐上北上的火车,一下子就到阿尔山,找到表姐夫,安顿好马上挣钱。他正在举目张望的时候,后脊梁骨被人重重的拍了一下,心里咯噔一下,会不会碰到黑社会的,大天白日的明抢名夺,想到这他的心都快要跳出嗓子眼。猛然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打消了他所有的顾虑。
“这不是老同学吗?几年不见,架子还挺大,我喊了你好几声,愣是没搭理我。”
曹绍武猛然醒过腔来,那声音闭着眼都能猜出来,那不是邢国旺吗?邢国旺跟他那关系可没得说,白天一起背着书包上学,晚上在一个被窝里来回滚。他俩没事的时候,比谁的牛牛大,每次都是邢国旺败下阵来。他吓唬邢国旺,牛子小那是和尚命,就是娶了媳妇,也没有孩子。吓得那小子蒙着被子呜呜哭号,还直接问爸爸,看见宝贝儿子满脸是泪的可怜样,就给儿子打气,老曹家小子没安好良心,只要长着牛子就能说媳妇,老曹家那小子再乱说,咱爷们就要抓住他,用菜刀把牛子剁下来喂狗。邢国旺找到了依靠,再比牛子大小,输得稀里哗啦的时候,邢国旺就用爸爸拿菜刀剁他牛子来威胁他,现在回想起来,还挺有意思,有时候都憋不住笑。
邢国旺小名就老九,他曹满金经常喊他“老九回家吃饭。”、“老九,给爸爸把簸箕端过来。”邢国旺他三姐叫邢月华跟他同岁,经常在一起玩。他喜欢喊邢国旺叫“老舅”,后来听人说“无亲不叫舅,叫舅就够受。”他先还没明白咋回事,后来越琢磨越不是滋味儿,当他再次喊他老舅时,突然翻脸一拳头打在我鼻子上,鼻血顿时从鼻孔里窜出来,用纸蛋子堵住鼻孔,血就从嘴里流,他的症状吓坏了邢国旺,用尽了各种土办法,才把鼻血堵住。曹绍武咽不下这口气,跟他说你把我打坏了,现在脑瓜子迷糊,看东西都俩影影儿,放学回家到你家炕头上躺着,天天打针吃药,让你姐给我包一个肉丸饺子,都得扒了皮才吃,我让你们和尚不得睡,姑子不得安。他的这些狂言诈语,都把邢国旺苦胆吓出来了,他哭唧唧的说“我求求你了。千万别到我家闹腾,我爸会把我屁股的。”他嘴里吐出一大块血块,落在脚下的石头上,用手指点点,声高气壮的说“王八蛋,你看看你下多么重的手,这可不是欺负你吗?我非得找你爸爸,非得给我掏药费。”邢国旺吓得没脉了,恨不得给他跪下磕头叫祖宗,哭哭啼啼,一下子熊了。他挠挠脑瓜子,打算绕过他,打狗还得看主人,更何况跟邢月华还挺好,因为这么大的一点小事,把伟大的阴谋全部泡汤得不偿失。他趾高气扬的说“看在你姐的份儿上,这次先饶了你,你个小崽子再给我拉硬,我可真不惯着你。”他贼心不死,做梦都想亲亲邢月华,尤其是这段时间,夜里总跟邢月华在一起,撕撕扯扯,卿卿我我,醒来身子底下黏糊糊的,耳红心跳,起早就自己洗褥单,呱唧呱唧,好像做贼一样,恐怕别人发现的秘密。
曹绍武缓过神,挥起拳头,照着邢国旺的肩膀子上,就重重的敲了两下,他依旧那么粗声高嗓的呜呜喳喳的瞎折腾。“你小子这些年,在外面发了财,就忘记老家乡这些人了。你这德性,就是腰缠万贯的亿万富翁,我也看不起你。人们经常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说说你,有多少年没回老家了。”邢国旺还是老样子,脸皮太他奶奶的厚了,用铁锨都挖不透,他的这些日骂的话,全不当吃颗小辣葱。“我说哥呀,你是我亲哥。这些年我可没少吃苦受罪,我姐夫虽然是大老板,他没少照顾我,因为我在外面乱搞,原先那媳妇不跟咱过了,我姐夫又给我张罗一个。那个坏种对我忒狠,都快赶上使唤牲口了,我是他奶奶的日夜在岗,小车不倒我就得一个劲儿的往前推。”他们正说话间,远处传来列车的鸣笛,他顾不得跟他说话了,准备随时迈开大步,抢占最有利的地形。邢国旺一把手把他拽过来,不容置疑的说“哎,你那也别去了,跟着我混好不好。”他人穷志高,哪怕到要饭那天,也不会奔着他下巴颏打悠千。“我土里土鳖的摸样,到哪里去,纯粹给你丢人现眼了。我这个人,属小鸡的刨着吃的命,只能靠力气挣钱,让我耍心眼子,就是整死我都不会。”他心里有些嫉妒,涌动着说不清楚的伤感。假如,他不顾曹满金和姐姐们的反对,执意上学考个中专,现在最少是学校老师,政府干部。如今可倒好,混得如此的凄惨,他家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家业飘零,在村里也是为漏斗户。邢国旺还是蛮有力气的,一把手拽住他的行李,也跟他耍起了牛B,眼珠子一瞪,大声说“咱们是不是光腚子伙计,你现在不如我,我帮帮你不行了咋地。你都扔下四十奔五十的人了,你就是再他妈的充好汉子也不行,到岁数了不服不行。你打着行李卷,下苦力你究竟能挣几个钱。你必须听话,咱哥们我还能给你当上吗?”
曹绍武心里才转过弯儿来,干嘛还那么要面子,都已经到了这步田地,真不能死撑下去。香兰那个瘤子,年前年后就得狠狠心割了,没有钱哪怕是磕头叫祖宗也得做呀,要是发生癌变,到哪里找那后悔药呀。长顺这孩子随他,相貌不咋滴,就是悟性好,进入初中后,年年都得奖状,班主任说照这样下去,考一个重点大学,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了可怜的香兰,为了孩子,他苦痛的放下他的臭架子,可怜的好像一条狗,晃荡着尾巴,乞求主人赏给一些好吃的。他软下来,眼神不那么敌视,显得格外的谦和。“我去哪里合适吗?再说咱们非亲非故,怕你为难呀。说一句实在话,这几年混得不好,好年天收,粮食不值钱,粮食值钱了,不是涝就是旱,灾荒不断,一年打那么一点点粮食,刚够度命。”邢国旺拍拍他肩膀“咱们是哥们,有我老邢吃的,还能让你饿肚子。别的不敢说,咱哥们在一起,肯定比你到外面打游逛锤要强呀。”
二
曹绍武做梦也没想到,在车站会碰到邢国旺,做梦也没想到,在他穷途末路的时候,会遇到故知呀。在这冥冥之中,好像有神灵在帮助他。他回首过去,真是不堪回首,在几个姐姐的娇惯下,他是这个家的宝贝疙瘩,在二十五岁之前,他是横草不捏,竖草不拿,一天到晚就知道玩。他从学校门下来之后,曹满金已经六十多岁了,因为几个闺女都找了好主,各个在家里又都能主事说一不二。他家的承包地全都是这几个闺女女婿,赶着马车,拉着犁杖,起早贪黑的给种地、拔苗、割地、打场。他好像一个公子哥,吃饱喝足叼着香烟,到商店跟一帮闲人凑在一起打扑克、戳台球。别人都羡慕他摊上几门好亲戚,真是太享福了。有人背后撇嘴,跟几个老娘们咬舌头说“一个小年轻的,现在到处逛洋灯,怕是遭罪的时候在后面呢?”教过他的郎老师说,挺好个人彻底白瞎了,家里大人要是不扯他后腿,最次能考上财校,闭着眼也得到大企业当会计,天天吃香喝辣。比现在可牛气多了。他不干活不管家务,就是再给曹满金和几个姐姐置气,不叫你们这些人拦着,肯定能考上中专。你看看三队的大刘新,学习还不如他,人家都准备考大学了,说话办事处处压他三分点,他处处比人矮半分。他就是要当大爷,就是要不学无术,就是要破罐子破摔。什么青春梦想,什么伟大目标,对他来说那都是扯淡。他家在当时在整个村子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富裕户。曹满金放出话,要给武子说媳妇。老人家喜欢叫他小名,从不喊他名字,直到长顺都记事儿了,他还这么喊。曹满金这一口风放出去,他家比大车店都热闹,保媒拉纤甚多,姑娘都普遍比他大,媒人都不约而同的说“女大三抱金砖”、“说个大媳妇,能把你们武子当成儿子哄”。曹绍卿大嫂子也跟着起哄,她也是保媒的行家,你别看她年龄才三十多,那张嘴能把死人说活“三大爷呀,你看看咱们家的老兄弟,那可是金枝玉叶呀,要模样有模样,要脑瓜有脑瓜,家里面要啥有啥,咱们家说媳妇,那可得翻开眼皮,好好瞅瞅,看着不顺眼的,就是大腿上绑着2000元钱,咱都不稀罕。咱们老曹家,可不是废品收购站,歪瓜裂枣,剜到筐子就是菜。”老爸特别高兴,笑得合不拢嘴,l着了魔似的说“这他妈孩子,就是会说话,你大嫂子那可是咱老曹家的门面,我们家武子说媳妇,就得照着你的模样说。”曹绍卿大嫂子嘎嘎笑,他觉得大嫂子有些不正经,他在说商店里就听有人叨咕,跟镇里的张站长有一腿,究竟是真是假,他整不太明白。他低着头不说话,满脸通红,爸爸曹满金有些不痛快,用眼袋锅敲打着木头炕沿邦“你小子越来越窝囊了,你大嫂子给你当媒人,你应该说一句谢承的话,你可倒好哑巴啦,咋还成闷葫芦了,我的老天爷呀,你可真他奶奶的愁人。”他有些不满,不是一般的不满,而是大不满,他还没玩够,说媳妇结婚,他就好像散养的驴驹子,戴上了笼头,一切就不得自由了;他结婚以后,那就是大人了,就好像戴上捂眼的毛驴子,一圈圈拉磨,想停就会有人用鞭子抽你。姐姐们隔三岔五就回到家里,当然都这结伴而来,几乎一个都不少,不是给爸爸拿回一只沟帮子烧鸡,就是给他买一条裤子。他心里有些压抑,不想跟相差二十几岁的妈妈级的姐姐们在一起拉呱。他跟她们姐们有隔代感,没有啥感兴趣的话题,打心眼里讨厌他们。他同班的同学,有些比他成绩还次的人,如今还在学校里念书,他却要结婚呀,要跟老婆在一起过日子,柴米油盐酱醋茶,种地拔苗割谷子收玉米清猪圈,日子过得寡味,没有一丝光泽,看不到前边任何一点点光亮。这些都是三个姐姐的从中作梗的结果,假如他继续上学,现在肯定坐在教学楼里,跟同学们一起学习,早晨闻着花香,在操场上跑步,在花丛里晨读。他多么渴望那一种生活呀,可是他的梦想,就这样被四个姐姐活生生剥夺了。他从心里对四个姐姐恨死了,一天天指手画脚,婆婆妈妈,不是这不对,就是那不行,动不动就说“我们家你三姐夫说了,只要好好听我们的安排,等咱老爸入土之后,在政府给你安排一个工作。”他心里在蹿火,那话等于没说,三姐夫在镇政府当司法所所长,他有那么大的权利。再说,爸爸现在又能吃又能喝,能一口气拉半亩地磙子,他老人家一定会健康长寿。再说,当着老人家的面,说出这样狗屁不如的话了,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他抓住三姐这个过错,大声跟她吵闹“三姐,我宁可一辈子种地,也要咱爸爸身体硬硬梆梆,吃嘛嘛香。我可不稀罕到政府上班,我就好好跟爸爸生活,当一个非常孝顺的好儿子。”三姐觉得自己的说秃噜嘴,让一个小孩崽子抓住把柄,顿时脸红耳赤不言语了。他占了上风,四个姐姐都觉得他别看人小,心里的鬼还不小呀.....曹绍卿大嫂子看着他,突然笑了,那笑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她用手巴掌重重的拍了拍他肩膀,妩媚的瞟了一眼“我说老兄弟,我说得这一个人,保准你一百二十个满意。”他低头不语,在给爸爸赌气,呼哧呼哧喘粗气。曹绍卿大嫂子似乎看出里面的故事,便不再绕弯子,直接就捅了出来“大嫂子说得这个人,在咱们这小地方,那可是数一数二的美,我一说,你保证乐得蹦高——”他提不起精神,对说媳妇有一种特别恐惧。爸爸被曹绍卿大嫂子给吊的不行,眼珠子瞪得老大,急不可待的追问“那姑娘到底是谁,你这他妈孩子,赶紧说呀,老闷着干嘛!”曹绍卿大嫂子这才说“邢国旺三丫头,那多漂亮,嘴一分手一分,在地里拔苗那次回来都不空手,挎着一大筐子菜,这几年年年都喂四口大肥猪。那人过日子,那可是没挑,咱们老曹家要是把她给说过来,老祖坟都冒青烟了,那可真是积德行善了。”爸爸笑了,非常可心的那种笑,一拍炕沿“你嫂子,我看行,只要人家老邢家没啥意见,我应承下来。”他觉得邢月华倒是不错,就怕人家不愿意,老邢家那可是过日子人呀,这些年他不着调,到处逛洋灯名声可不太好呀。曹绍卿大嫂子扭动的屁股来到他跟前,一股子雪花膏的气味,呛得他直恶心“老兄弟你看邢月华行不行,只要你点头,我就豁出我这张脸给你说去。”他顿时兴奋起来,牛子一下有了反应,便红着脸说“嫂子,我就怕你说不成,你要是把这事办好,我给你杀四个牙的大公鸡好好谢承你。”爸爸笑了,佯装生气的说“瞧瞧你那点出息!”
曹绍卿大嫂子还真把邢家的人说动了,也就是七八天邢月华跟我搭伴去县城里买东西。爸爸心里鬼得很,直接给他腰包里装了500元,悄悄跟他说“傻小子,你呀别太抠门,别太老实了,老实人吃亏。”爸爸说完就笑,神神秘秘的笑,肚子里藏了一下子坏水。他跟邢月华走出村外,沿着山路走,正是草长莺飞花红柳绿的好时候,空气清新山美如画。他贼眉鼠眼的向四外看了看,清晨的深山没有人,野鸡在鸣叫,惊醒的野兔在逃窜。他拉住邢月华的手,身子在一点点靠近,身上的气味真好闻,新洗的头发,有一股清香味,比绍卿大嫂子的味道好闻多了。
“我早就对你有意思,你不搭理我,好像一个骄傲的公主皇姑金枝玉叶,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滚犊子,你呀俩毛钱买一个茶壶,就是嘴好。你呀,不准忽悠多少个小姑娘了,现在又想忽悠我,我可告诉别他妈的大米饭不熟欠焖,摩托车打不着火欠踹。”
“我对你都是真心得,不信你问问老兄弟,想当年他把我揍得顺着鼻子蹿血,要不是看在你面上,我肯定跟你放赖,躺在你家炕头上,吃一个肉丸饺子,都得剥了皮。”
曹绍武专说赞美的话,他觉得凡是人都喜欢奉承,说着说着邢月华就放松了警惕,彼此越来越近乎。在那颗百年老榆树下,想起了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人家请老树做媒,他何不来一个,在老树下疯狂的拥抱,让这个老树见证他们的清纯而又美丽的初吻。他紧紧的抱住邢月华,粗暴的亲吻,没想到邢月华急眼了,用手在他胳膊上拧了一个大紫疙瘩,但是他还是紧紧抱住她,在脸上好像鸡啄小米似的亲了一下。
“你他妈的要死,在这样不讲究,我告派出所把你抓起来。”
“派出所敢抓我吗?只要是在你身体里提取不到,我的那东西,你就是污蔑,你就得蹲大牢,看看谁吃亏。”
“你真坏,坏死的坏。”
曹绍武跟邢月华在城里买了些东西,在饭店吃了饭,还在包厢里看了一场录像。那时候,最时兴看录像,有钱的都会包间,老板会根据人们的爱好放片子,他在包间里选择了一个挺刺激的三级片,在黑暗中他们撕下面纱,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他发了毒誓,要娶邢月华当老婆,天老地荒,相爱一辈子。他隔三差五,还到邢家吃饺子,好像他们之间的亲事,已经是板上砸钉,牢牢邦邦,谁也推翻不了。
大姐拉着三个姐姐前来看爸爸,吃完饭姐几个没事就在一起唠嗑。爸爸狗肚子盛不了三两油,盘腿坐在炕上,叼着眼袋闭着眼睛,吧嗒吧嗒抽烟,煞有介事的咳嗽几声,裂开嘴笑了。“你兄弟这亲事,就不用你们姐几个犯愁了。他已经和老邢家的闺女好上了。老邢家那闺女,人长得俊儿,还能过日子,武子说了这样媳妇,肯定享一辈子福,祖上有德烧了高香,积了大德。”大姐曹春霞一听就蹦高了,脸色骤变,指着爸爸的鼻子说“爸爸,你是不是老糊涂呀,别人不知道老邢家啥样,你还不知道,邢凤斌老婆,那可是有名儿的烂板凳,谁给钱就让谁上,出了名的大汽车。他家家风不好,你让武子娶他家闺女,那有好吗?当一辈子活王八,受一辈子窝囊气。”曹春霞气得肚子咕咕响,想当初爸爸就跟邢凤斌老婆有一腿,把家里的蜂蜜、猪肉、小米等等零碎东西,藏着背着给邢家送去,妈妈叫嚷着到他家翻出来,两个女人好像两个掐架的大公鸡,撕破衣服挠破脸。
爸爸彻底蔫吧了,低着头好像犯错误的小学生,半天也不言语了。曹绍武觉得大姐曹春霞纯粹是鸡蛋里挑骨头故意挑刺,他来回走了几步,声音不大不小,跟大姐对抗“大姐呀,你看看我也不是三岁小孩子,这也要你管,那也要你管。我都二十多了了,已经是大小伙子了,应该知道该咋处理事情,你用不着你胸脯子挂罩莲多捞那份心了。”他不服气,看不惯四个姐姐,婆婆妈妈的样子,这还是他的亲姐姐吗,简直就是一群没事找事的太监。他说媳妇,当然他的自己说了算。可是,他的四个姐姐,却要用世俗的刀子,把他和邢月华这层关系活活的割开。他愤怒了,像一头猛兽,扑向他四个妖魔化的姐姐。
大姐曹春霞脸色沉了下来,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眼泪顺着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滴落下来,用手背擦一把抹一把,委屈的好像一个被冤枉的孩子。曹绍武坚硬的心,在大姐的眼泪中顿时酥软了,他还离不开姐姐们的呵护。在他四岁的时候,妈妈就死了,据说是想不开喝药死了,而且喝得是毒性最强的敌敌畏。没有妈妈守护的漫长岁月里,都是姐姐们的陪伴下度过的,那时大姐都已经结婚,他外甥常在还比他大两岁。人家都说老嫂比母,他这是老姐比母,到什么季节穿什么衣服,换什么鞋,处处样样都侍候的合合适适,让附近的婶子大娘都羡慕的不得了。他赶紧掏出干净的手绢递过去,眼睛也转泪了,轻轻的说“大姐,你别哭了,我以后再也不呛你肺管子了。”曹春燕抽抽嗒嗒的说“老疙瘩你可得长心呀,咱家妈咋死的,你难道就一丁点不清楚。不是你老姐多事,除了老邢家的闺女以外,其他任何人我都不反对。你娶老邢家的丫头回来,咱妈在地底下那不得气炸肺了。”他不明白这里究竟咋回事,还不好问姐姐们,爸爸老实得好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躲在墙旮旯里,连大气都不敢喘。在太阳压山的时候,老姐才带领三个姐姐打道回府。
在吃晚饭的时候,爸爸才缓过神来,抬起那张褶皱纵横的老脸,平和的笑笑“你们之间没发生啥事吧?”啥事?曹绍武顿时就红脸了,不敢正面回答,低着头小心翼翼的喝着小米粥。“你小子也是,八字没见一撇,你和她就鬼混在一起,那叫什么事呀。万一人家一翻脸,告你个强奸,我的傻孩子,你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他把眼一瞪,不把这件事当吃一颗小啦葱。“爸爸,我们谁都没强迫谁,你情我愿,你们管不着。”爸爸从炕上拿起笤帚,照着他脊背就抽了下去,喊破嗓子嚷吵“你个孩崽子,办事咋就那么鲁莽。”他觉得爸爸太坏,当初就是在他的蛊惑下,稀里糊涂把生米煮成熟饭,如今他还倒打一耙,什么人呀。他不服气,装疯卖傻,想戳他的痛处,关于老爸和邢月华妈妈之间,肯定有很多丑事。“爸,你告诉我,我大姐为啥死活不让我跟邢月华结婚,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猫腻!”爸爸愤怒了,压抑多年的郁闷火山一样喷发了“那有啥猫腻,你妈不想活了,死是该死,哼!”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爸爸对妈妈不屑一顾,他揪住爸爸的衣领子,咬牙切齿的问“爸爸,你凭啥对我妈那样。”爸爸蹲在地上,捂住脸,满脸是泪“你妈竟往自己的脑袋上扣屎盆子,不但他自己命搭上了,小华的妈妈也上吊死了。”
曹绍武不敢往下想了,他不明白为啥老邢家的人,对他还那么好呀。现在,他还不清楚,父辈之间,究竟发生了,哪些不可思议的事他不敢继续想
三
邢国旺对曹绍武比亲哥兄弟都亲,掏了高价给他补了卧铺,那张嘴皮子如今特别好使,三下五除二就把下铺的哥们摆平,他们这对光腚伙计,凑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他囊中羞涩,想买两个面包蒙混过关。邢国旺这家伙,在外面就不管那些了,要了一个烧鸡,三袋熏猪爪,拧开一瓶大瓶牛二,看了他一眼。
“咱是哥们,你就别跟我装好不好,该吃吃该喝喝,你把心放在肚子,我管你吃喝还没啥问题。”
曹绍武挠挠脑袋,憋得满脸通红,想耍几句嘴皮子,仔细一琢磨,你有啥耍的吧?没钱没权,你就说得天花乱坠,能顶啥用吧。邢国旺先嘴对嘴咕咚喝一口,把酒瓶子传给他,一瞪眼珠子“赶紧喝,你跟别人装行,咱啥关系能跟我装。”他不多想,为了显示他英雄不减当年,一仰脖股咕咚咕咚连着喝两个大口,瓶子里的酒顿时下去一大块。邢国旺笑了,嘿嘿笑了,显得特别开心。“你小子,喝酒还那么牲口,我服你了。别光喝酒,咱们俩把这些东西,咧着腮帮子全都给造光了。”他有些飘飘然,不再拘谨了,说话也仗义多了。“我还是我,腿不疼,腰不弯,说话赶上小钢炮。”他张牙舞爪,不把邢国旺放在眼里,他们肆意喧哗,引来很多旅客的围观,他不在乎他就是一个头顶高粱花长大的庄稼人,啥规矩都不明白。邢国旺这家伙,也没啥修为,充其量就是个混混。他吃了两个鸡翅外加两个猪爪,打着饱嗝,抓起酒瓶子,一仰脖咕咚咕咚,好家伙一下子干了小半瓶。他有些迷糊,酒力不支,便倒在卧铺上和衣而眠。这几天,他张张罗罗外出打工,身心早已疲倦不堪,喝了些酒便如此这般。他卧铺上不消二分钟,便鼾声如雷,进入了梦乡。
曹绍武醒来时,车窗外广阔的平原被大雪覆盖,天边的云彩被太阳映红。他看见邢国旺在临窗的椅子上,眺望着窗外若有所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没启封的烟,很平常的那种,习惯性的扔给他一支,邢国旺赶紧摆摆手“这里不能抽烟,憋一会,八点多就到地方了。”他窘迫的笑了,觉得还是有些见识短了。邢国旺冲着他笑笑“你小子真挺好,张开嘴巴就是吃,闭上眼睛就睡。哎呀我的那老天爷,那呼噜打的都赶上打霹雳了。睡要是跟你在一个屋睡觉,那可是倒八辈子血霉。”他笑了,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那种傻笑。邢国旺兴奋的说“我给我姐打电话了,说你要跟我们入伙,她高兴的不得了。”他机灵了一下,心里好像被针扎了一下,他觉得他就是一个负心汉,这些年一直在反反复复折腾自己,恨四个姐姐,埋怨爸爸平白无故孽生跟邢家的是非恩怨。往日的情景,又好像复活了,非常清晰的在眼前浮动......那是多么美好的夜晚,圆圆的月亮,在天空中慢慢的走动,清风从田野里吹过来,能闻到庄稼成熟的香气,能闻到苹果、鸭梨的香甜。秋虫鸣叫,如同水花在草丛里飞溅。他和邢月华不得不分手,大姐曹春梅掐着腰跺脚骑在邢家破口大骂,他们那种灵与肉的联系,已经彻底被割断。他未语泪先流,死的心事都有了。“咱们都收心吧,各过各的日子,从今往后,谁也别扯扯谁。你大姐这么闹,咱们还能吗?”他在邢月华跟前还能说啥呀,以前那些誓言,全都被四个姐姐破坏了,被撕扯的粉碎,漫天轻轻飘飘的飞。“你呀,别想那么多。我爸爸说了,你爹是好人,他跟我妈之间啥都没,特别的清白,都是那些老娘们没事给扯扯出来。再有,你爸爸是我们邢家的大恩人,当年我妈妈生我弟弟的时候,要不是你爸爸,私自挪用大队公款,大人孩子早就没命了,我是来向你们报恩的。”他满眼是泪,恨不得钻进田鼠洞里.....他摇晃着脑袋,看着邢国旺那种倦容的脸问“你姐,现在咋样?”邢国旺笑了“咋样,挺好的,吃不愁喝不愁,日子过得挺滋润的。这日子再好,也有不随意的地方。这大老爷们,有点糟钱,心就花花。你别那样看着我,你有钱当大款那天,也是那屌德性。我姐夫在外面找了一个小的,孩子都他奶奶的上小学了。我就劝我姐姐想开些,寻死觅活有啥用。为了孩子,就得好好活。你要是跳河钻火车,那死非常容易,那孩子不遭罪了吗?我跟我姐说,你不管咋闹,孩子投娘来奔爹来,缺爹少娘的,那不是再造孽吗?”
曹绍武心里沉了一下,他不敢往下想邢月华的事了。他过得到时平稳,平淡如水,好在香兰是个贤妻良母,好在有一个争气的儿子。
列车进站了,邢国旺收拾着东西,跟他磨磨唧唧,他有些烦,这么多年了,邢国旺这狗日的脾气秉性没改,俗话说得好,生姜改不了辣味。
“你看,我姐。”
曹绍武看见了,邢月华那熟悉的身影,虽然她变得有些富态,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的心提到嗓子眼,我的那个娘亲呀,我该咋跟她说话呀。真后悔呀,一点准主意都没有,他该咋跟她说话呀。想到这些,他的脸红了,心颤抖不已。
欢迎光临文学風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