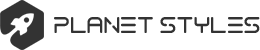啊,小村(梅花君子)
啊,小村(梅花君子)
600)makesmallpic(this,600,1800);" height=398>
啊,小村
文:梅花君子 编:一缕清风
600)makesmallpic(this,600,1800);" height=40>
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外面散步权当锻炼。我散步的路线有两条,第一条顺着山路,不畏艰险,连翻三个山头,尽览奇峰秀色;第二条,沿着公路不断南行,不拐弯,不抹角,公路两旁,树木葱茏,看朝霞映日,炊烟袅袅,听犬吠鸡鸣,领略农耕恬静之美。
4月13日晨起,我走出室外,清风徐来,浓浓淡淡的杏花香味,就扑入心脾,顿觉风清气爽,心旷神怡。昨日早晨我已经登峰越岭,看遍山间杏林花海之壮观。今日倒要改变路径,沿着公路南行,看看不一样的景致。我行至兴哈线36公里处,有一岔道,新修的通村水泥路,如同一条飘带,镶嵌在空旷的田野上。举目远眺,高耸的树木,露出红瓦高房,牛哞马啸,飘入耳边。我忽然有个想法,何不信步到前边小村,随意行走,或许会有新发现,能欣赏到别致的风景,倒也是一种难得的情趣。
走了十多分钟,村落就在眼前,杨柳树还没萌发新绿,远远看上去,被一层薄薄的淡绿色的烟雾所笼罩,如梦似幻,好像一首生动的田园诗,宛如一幅生动的小村迎春图。山间松林荒草丛中,野鸟啾啾,参天大树上,三五只喜鹊,站在杨柳枝头,叽叽喳喳,很自然的想起了“喜上枝头”这句喜庆吉祥的老话。
这个小村,树木繁茂,杨树柳树,都不是近些年栽植的,存在最少也有好三十多年了。高大的树干,繁茂的枝桠,鸟窝随处可见。很多农户的院子里,栽植了杏树、李子树、桃树、苹果树,等北方地区比较常见的果树。晨风在枝头上徘徊,粉嘟嘟的杏花,伸展在墙外,在与清风跳舞。淡淡的杏花特有的香气,紧紧得将我包围起来,看花闻香,该是多么的惬意呀。
这个小小的村落,宛如塞外桃源呀。现代文明的脚步,迟迟没有光顾,依山而居的小村。空气清新,绝对呼吸不到,现代工业排放的PM2.5,听不到轰隆隆、地动山摇的设备轰鸣。这个小村,如此地宁静安详,宛如养在深闺的小家碧玉,纯美而又安静,没有让夫婿觅封侯的功利欲动。
我仔细打量着这个小村,质朴、平实,在周边很难再见到的小村。这里的民居,错落有致,房舍围墙多姿多彩,应该说是民居发展历程的一个微缩的长廊。这里残缺的凸凹不平的板打土墙,有用瓤秸泥垛成厚重院墙。我还惊奇的发现,居然还有上个世纪初的老式瓦房,青色小瓦,白灰抹面,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却依然英姿飒爽。五十年代的泥草房,好像逆着时光,走进了祖辈生活的那个年代.....当然了,大多数的民房,都是高大敞亮的新式瓦房或者平顶房.很多人家的房顶上,都安着太阳能热水器。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安着“十个全覆盖”配发的户户通小锅。人们顺手一拧,就能用上热水,打开电视,就能看到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
乳白的炊烟,像一条弯弯曲曲的玉带,萦绕在树木繁茂的枝头。浓浓的饭香,从院落里飘出来。久在农村生活的我,一闻到久违的饭香,就能判断出那是用大锅捞出的小米饭。这个饭香多么的亲切,勾起我多少美好的记忆。童年的我,就是在这样的饭香中苏醒,吃着这样的小米饭长大。如今呀,童年中的饭香,已经成为记忆,在现实中能吃上,不上化肥,不喷农药的小米,简直就是一种过高的奢求。女主人打开大门,到门前的小菜园,拔了十多颗羊角葱。啊,她这是要用葱蘸着自家烧制的黄豆酱,吃着肉透透的 小米干饭,想想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到了秋天,到门前小菜园掐几片嫩绿的白菜叶、几颗芫荽、两颗大葱,洗涮干净,用新小米干饭裹一个菜包,那倒是任何饭店都做不出绝佳的美味儿。
随着吱呀一声响,女主人推开大门,到门前的垃圾池倾倒垃圾。院子里窜出一只体型健壮的白公鸡,忽闪着翅膀,跑了出来,身后跟着一群母鸡,钻进沟壑上面的树林里,刨食着草丛里的天然食品。如零星的草籽,蠢蠢爬行的小虫子。精力旺盛的大公鸡,追逐着一个秀丽的母鸡,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爱情表演。在这么好的环境下,这些母鸡们,真达到了,渴了喝露水,饿了吃蚂蚱,非常洁净的境界。如果在三十年前吃上这样的纯天然鸡蛋,那倒不是啥难事,在各种速生饲料、各种添加剂的包围下高度文明的今天,硕大漂亮的饲料蛋,堂而皇之的进入百姓餐桌。在市场上,商人们都在鼓吹,所售的鸡蛋都是笨鸡蛋,但是吃到嘴的时候,总是与我们儿时的味觉相差甚远。有时间,我一定到这个小村那户人家买鸡蛋,炒出的鸡蛋,嫩黄清香,那味道肯定胜过饲料鸡蛋好几倍。
在这不显眼的村落里,听到了丰富的鸡鸣狗叫,这些生动的声音,那就是一种久违的难得的幸福。在大多数的村落,原始的声音和节拍,已经被现代农业文明慢慢的逼退。现代农业的发展,机械代替了,人扶犁杖,牛拉犁,人点种的原始化的耕种方式。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们的子孙,恐怕就连种地的犁杖、点种用的点葫芦头、耪地用的锄头,一点都不认识了。因为稀少,看到这些农耕家具,觉得格外的亲近。看到这曾经熟悉的一切,都会唤起我的青葱岁月哪些美好的记忆。在惠风和畅的田野里,一挂犁杖在瑰丽的阳光下,在松软的土地上前行,铮亮的犁铧尖划破了沉睡的土地,金色的种子均匀的散落在新开得垄沟里,不偏不倚,好像一条金线那样笔直,细碎的粪土,给种子盖上一层温暖的棉被,在和风细雨,破土萌芽,庄稼人的心情也会随着满地的庄稼的健壮而起伏飘荡。
在现代文明如潮水般,将古朴的村风侵蚀殆尽的时候,能在身边发现这么一个,静谧、淳朴、执着的小村,在发展的浪潮中,保留了特有的发展轨迹。树木包裹着小村,古老和现代,互相包容。或许因为这些,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在我的眼里更像一个农村。她恪守着一个原则,始终没忘记“农村”这个身份,没有迷失自我。以其特有的个性,让我沉醉其中,假如时间允许,我倒真想在这个村,找一户人家,好好住上一段时间。跟他们一起,上地拔苗,挥着镰刀收庄稼,拧着辘轳打水,挑着一担水,行走在瓜果盈枝,花香满天的水泥路上,该是多么惬意的一件好事。
文学风网站欢迎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