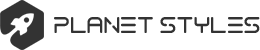饥荒岁月(梅花君子)
饥荒岁月(梅花君子)
饥荒岁月
文:梅花君子 编:一缕清风
我小时候,大多数人家都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困顿生活。我家里的日子也是异常的紧巴,妈妈做饭算计着做,早晨做啥饭,中午做啥饭,晚上做啥饭,一顿饭下多少米面,用称量着做。妈妈会打理能算计,细水长流,在饥荒岁月里,我没有像其他人家的孩子,被饿得面黄肌瘦,排便困难被憋的嗷嗷叫唤……至今回想起来,很多事情,在脑海里生动呈现,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神使鬼差的促使我,写下这一段饥荒岁月零零碎碎的记忆。
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成了重点保护对象,姐姐嘲笑我是大熊猫。我不在意这不雅的外号,哪怕管我叫大狗熊,只要让我吃香喝辣那也无所谓。眼见着粮食没了,妈妈好像会变戏法,今天给我们做高粱面汤,明天给我们贴小米干粮,再后天让我们吃一顿杂合面的蒸饺子。我觉得妈妈一定是神仙转世,在弹尽粮绝的关键时刻,会像神仙似得能点石成金。我怀着好奇心,躲在旮旯里看看妈妈如何化腐朽此为神奇。快做中午饭的时候,妈妈拿了木升不慌不忙的走进了草屋子,在开草屋门的时候,紧张的看了又看,确定没有异常之后,钻进草屋子,过了好一会才出来。我趁妈妈不注意,钻进草屋子,在一堆秫秸后面,发现了两个大缸,一个缸是玉米面,一个缸是小米。我兴高采烈的跑到妈妈跟前,说出我看到的秘密。妈妈顿时把脸拉了下来,非常严肃的说“你不能出去瞎咧咧,小心我扯你嘴巴。”我怕妈妈打我嘴巴,把看到的秘密烂到肚子里。
妈妈勤快是出了名的,邻居们大娘婶子们夸奖我妈妈“嘴一分,手一分。”刚开春的时候,妈妈拿着镰刀到山上、沟崖处,一筐筐掳榆钱,回到家里仔仔细细把虫子和残品挑出去,用干净水洗了,用玉米面和了,放上葱花、咸盐、荤油给我们做榆钱干粮。我最喜欢吃榆钱干粮,有时候比大人都能吃。放学后,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掀开锅盖,拿着榆钱干粮跟伙伴们炫耀。每个人自然都分到一小块榆钱干粮,我成了大家拥戴的领袖,拉帮结派,哄哄嚷嚷到处滋事。每次在野外开战,我带着我的兵将把人打哭,大人领着孩子,跟我妈急头白脸理论。我妈总是满脸憨笑,掀开过拿出榆钱干粮,让人家尝新鲜。一场场异常激烈的矛盾,在妈妈的微笑和榆钱干粮的互换中得到平息。
妈妈在春天除了用榆钱做干粮,还会用榆钱做面汤。妈妈过日子仔细,她经常给爸爸上课“过日子,不能有米一锅,有柴一灶,要细水长流,掐算着过日子。”妈妈烧开一锅开水,灌满暖壶就便将和好的面蛋,均匀的洒向花花翻开的锅里,在均匀的洒满榆钱。妈妈,很娴熟的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往下做,一大面盆面汤,三下五除二就非常轻松的做好了。榆钱面汤吃到嘴里,感觉滑滑,特别香甜。邻邻居居的婶子叔叔,闻见榆钱面汤的味道,便找一个借口,笑嘻嘻串门。妈妈总是热情的给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汤,婶子叔叔先拿捏一番,妈妈便说“过门槛吃一碗,你客气啥,要是再扭扭捏捏,拿腔摆怪,就不许你们叫我嫂子。”来人便仗义的端起碗,秃噜秃噜吃一碗,吃得真是舔嘴咋舌。妈妈也不再让,来人走后,自言自语说“给你一碗尝尝,那也就是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一张脸,我可不能管饱。我家的粮食也不够吃。”
槐树花开会有一股股甜丝丝的香气,从山坳沟壑里飘到房前屋后。妈妈在队里干活无论有多忙,一筐一筐往家挎槐树花。槐树的枝杈长满了尖尖的刺刺,稍不留神,就会把衣服挂出个大口子,手心手背被划得鲜血淋淋。妈妈不畏其难,一天中午挎回一筐子。妈妈的脸划破了皮,手也流血,便哭着对妈妈说“妈,你别掳刺槐花了,脸都刺破了,手也弄流血了,那多疼呀。”妈妈满不在乎“傻小子,你哭唧唧的干啥。干活吗,蹭块皮,划破肉,那都是正常。傻小子,你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吧,妈妈这点小屁伤,离心大老远,一顶点事都没有。”......我最喜欢看,妈妈做槐花蒸饺了。先把白白的槐花,倒在笸箩里,一点点摘,除去杂物,包括虫子,小棍子,被虫子咬残的花瓣。然后把槐花倒在一个黑色的瓦盆里,浇上井凉水,用长把勺子,反反复复搅动,再捞出来沥水。妈妈点着柴火,我坐在灶前的蒲团上,咕咕哒哒拉风匣。快开锅时,妈妈将槐花倒进锅里,来回折个,然后再捞出来,用笼布裹住槐花,放在菜板上,双手用力压揉,水顺着笼布哗哗的往下流......妈妈把槐花蒸饺,热气腾腾的端上饭桌时,妈妈嘴角上挂着笑。她看着我,一口接一口吃槐花蒸饺时,总是鼓励我“多吃几个,再多吃几个,长一个大个,身大力不亏。”如今,我已经有些年头没吃槐花饺子,今天春天我老婆特意从老家掳了槐花,给我做一顿槐花饺子,各种作料齐全,却再也找不到当年那种感觉了。
在粮食稀缺的年月,什么东西都可以入口。我家的房上有块山地,种庄稼不长,于是就种了紫花苜蓿。刚种完地,嫩嫩的苜蓿芽便闹哄哄的长出来。这些苜蓿芽成了人们充饥解饿的好东西。左邻右舍的嫂子婶子们,利用黑天的时候,拉帮结伙到苜蓿地挖苜蓿芽。队里为了保护革命的胜利果实,就派杜绝户看苜蓿。他无儿无女,大公无私,属于秃子楞瞎子狠的那类人。每天总能抓住几个偷苜蓿的贼,杜绝户用大脚丫子,把框子踩得支零破碎,还把头苜的贼,一个不落的上报队长那里,开会批斗,扣工分。我妈妈也去挖苜蓿芽子,但是跑单帮。那年,我跟妈妈作伴挖苜蓿芽子,不料被杜绝户逮住。他看了我们一眼,放低声音说“挖满一筐子赶紧走。”杜绝户说完转身就走。在饭桌上吃苜蓿芽子玉米饼子,我挑头说起我们被杜绝户抓的事情,妈妈满脸通红。爸爸很生气,跟妈妈拍桌子,爸爸是队委会成员,必须给革命群众起带头作用“你就那么馋,馋就拿鞋底子往嘴巴子上打几下。”妈妈不言语,平静的吃饭。这事没几天,杜绝户就拎着大包小包被子棉衣服让妈妈拆洗。爸爸就妈妈偷挖苜蓿芽子事件,狠“斗”杜绝户私字一闪念,嘚嘚咕咕说了一大堆革命话。杜绝户却挠挠脑袋辩护“现在家家户户都不够吃,偷苜蓿那是没办法的事儿。只要是不成群结伙去偷,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妈妈挖苜蓿总喜欢拉单帮,原来她摸透了杜绝户的心理了。若干年后,我猛然想到,我妈妈年年免费为杜绝户做棉衣服拆洗被褥,那是再还欠情呀。
耪地的时候,家里粮食就见底了。妈妈非常淡定,不着急不上火,在人们歇息的时候,她挖猪毛菜掳树叶,回到家摘了根须,洗去泥土,拌了玉米面做干粮饼子吃,菜多粮食少,但是妈妈会调配,酱油、荤油、花椒、大料佐料放全,咸淡合适,格外的好吃。妈妈在家里偷着养了五只大母鸡,每天至少都能捡到三个鸡蛋,中午饭总能吃到一盘韭菜炒鸡蛋。我记得特别清楚,妈妈在端炒鸡蛋前,好像做贼一样,前后左右看一个遍,门轻轻的插上,再轻手轻脚把鸡蛋端上来。我很傻,总要高兴的喊叫,妈妈总训斥我,说我狗肚子盛不了三两荤油。我却不长记性,一看到金黄色炒鸡蛋,兴奋地用筷子当当敲碗,要做欢呼状,妈妈用手指点我鼻子,小声而严厉的训斥“你再喊,把鬼招来,让你饿肚子。”在妈妈的眼里,闻着香气,敲门而进我的那些伙伴们,统称为馋鬼。妈妈骂我是调皮鬼、捣蛋鬼、傻鬼。在她有限的语汇里,鬼不是贬义词,相对来说应该有褒奖的成分。我在妈妈的警告下不再闹腾了,手里拿着菜饼子,就着喷香的炒鸡蛋,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我发现,爸、妈、姐吃鸡蛋,都是吃一小点点,几乎全用咸菜下饭,那盘炒鸡蛋几乎全让我吃了。妈妈看着我吃饭的样子,嘴角上挂着笑,总在说“好小子,多吃点,好长大个,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你。”
妈妈年年都喜欢在自留地带豆角,拔苗耪地费事费工,爸爸埋怨妈妈如何如何,他却笑而不答,却年年在自留地带豆角。农历六月以后,几场倾盆大雨过后,玉米便咔咔拔节旺长。豆角子也跟着长。妈妈看地回来说,“咱家的豆角子开花了,紫色的小花一嘟噜一串的,带这些豆角子肯定能够全家吃。”全家人都沉浸在美妙的期待之中,豆角子不但当菜吃,最主要的还能当饭扛饿。十多天后,妈妈天天贪黑挎回一大柳编筐豆角。一向矜持寡言的爸爸,紧锁的眉头也顿时舒展开来。他坐在桃树下,主动承担了摘豆角的义务。早晨我还没起被窝,那股浓郁的香气,就顺着门缝钻进来。我顿时睡意全无,洗手洗脸,当妈妈的跟屁虫,嘟囔着要吃豆角。饭少我们就以豆角为主,一大铝盆豆角,被全部吃光。每次炖豆角,妈妈总在豆角里放几块腊肉,这腊肉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为我嘴里的美食。我那时真是一个得一望二不知足的人。我反复的说“妈妈。我要肉肉,要肉肉。”爸爸心烦了,筷子当当的敲着碗,狠狠的说“下次炖豆角,一块都不放,这孩子让你惯的一点人样都没有。”妈妈不接爸爸话茬,总是给我许愿。那天上集给我卖大麻花,买一大把糖块.....过了立秋,豆角就吃不过来了。豆角的豆子格外饱满,妈妈偏心眼,每次都特意给我留一碗豆子特别的好吃,直到现在我保留着吃豆角豆子的习惯。
立秋过后,总算看到了希望。虽然年景不好,如干旱、雹灾、虫灾等等,都在消减着收成。爸爸蔫头耷脑,为工分不值钱犯愁,为完不成公粮任务愁,为家里这些张嘴吃饭犯愁。妈妈却是一个典型的乐天派,不知道啥叫犯愁。妈妈跟我说再过几天,就可以吃烤玉米。妈妈这话说完还没过五天,妈妈就把嫩玉米掰回来,用铁筷子穿上,放在火上烤。妈妈既要往锅里贴玉米饼子,还要照看灶间的玉米别烤糊了,经常进行转动。饭做熟了,玉米也烤好了。烤玉米金黄色,一个玉米粒都不焦糊,亮晶晶的好像一粒粒珍珠。我在拿着烤玉米在大门外显摆着吃时,总会招来一片赞叹声“小子,你妈可真巧,看看这玉米烤的真好。能不能给二娘吃一口。”我总是把玉米藏在背后,大声喊“这是我妈妈给我烤的,就是不给你吃,把你大牙馋掉。”说完,就赶紧往院里跑。二娘不追我,笑嘻嘻看着我“这臭小子,真嘎真嘎。”......如今,行走在繁花的街市上,也有烤玉米,也给女儿买过,但是吃着远不如妈妈给烤的香。
自留地的黄豆鼓豆后,也正是玉米成熟的时候。妈妈总是起早到自留地把玉米棒掰下,用化肥袋子扛回来。我们吃早饭,妈妈就咔咔的把玉米棒扒得干干净净。妈妈冲我笑笑,好像变魔术似的,从化肥袋子里面掏出一堆绿豆夹。“儿子,这是啥。”我顿时兴奋起来,饭也不吃了,哧溜一下从炕沿溜下来“妈妈,毛豆。我要吃毛豆。”爸爸怪起妈妈来“你呀,竟干烧香惹鬼的买卖,瞧瞧这孩子饭也不好好吃。这孩子让你惯下去,非瞎长不可。”妈妈不在乎爸爸的埋怨,用手在我脸蛋上摸摸“傻儿子,赶紧好好吃饭。你瞧瞧这脸蛋瘦的好像皮包骨,再不好好吃饭,二妮就不给你当媳妇了。”二妮比我小七个月,张家婶子给我许过愿,二妮长大之后,就给我当媳妇。我听了这话,马上回到炕上,把一碗饭吃得精光,比小猫舔得都干净。我举着碗给妈妈看“妈妈,我吃完了。”妈妈紧紧抱住我,在脸上响亮的亲一口“我大儿子真有出息。”
中午妈妈便给我们端上热乎乎的玉米棒、一盖帘毛毛豆。妈妈把毛毛豆给姐姐和我分开,我那份舍不得吃。妈妈睁大眼睛看着我“儿子,毛毛豆咋不吃。”我笑了,很可爱“妈,这毛毛豆给我媳妇吃。”妈妈笑了,笑得直不起腰。姐姐用手拨弄两个脸蛋“不要脸,小流氓。”我委屈的哭了,妈妈把我搂在怀里掉眼泪,她假装追姐姐给我出气,姐姐跑出了家门,我便破涕为笑,忘记了所有的事情,把我的那份毛毛豆吃得干干净净.....
在饥荒的童年里,因为妈妈的勤劳睿智,让我逃过了饥饿,对吃不饱穿不暖,没有任何印象。日子好起来之后,妈妈特别节俭,每年都要储备粮食,她是被饿怕了,看着囤满仓流的粮食,她总是笑了,反反复复说“仓里有粮,心里不慌。”我结婚后,有了孩子。妈妈对孩子要求很严,当孩子剩饭时,妈妈总是严肃的说“孩子,别剩饭呀,剩饭找对象找一个麻子蛋儿。”千方百计让孩子把饭吃掉,孩子实在不吃,她就端起剩饭吃得干干净净“好年月想着赖年月,粮食是好东西,糟蹋粮食有罪呀。”妈妈不会说大道理,她经历过饥荒岁月,总是在现身说法。如今,我也养成了好习惯,就是在单位吃饭,从不剩饭剩菜,顿顿都是连菜汤也不剩。我想,虽然饥荒岁月已经离开我们好长时间,但是不浪费要勤俭对我们还是挺实用的。
我小时候,大多数人家都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困顿生活。我家里的日子也是异常的紧巴,妈妈做饭算计着做,早晨做啥饭,中午做啥饭,晚上做啥饭,一顿饭下多少米面,用称量着做。妈妈会打理能算计,细水长流,在饥荒岁月里,我没有像其他人家的孩子,被饿得面黄肌瘦,排便困难被憋的嗷嗷叫唤……至今回想起来,很多事情,在脑海里生动呈现,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神使鬼差的促使我,写下这一段饥荒岁月零零碎碎的记忆。
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成了重点保护对象,姐姐嘲笑我是大熊猫。我不在意这不雅的外号,哪怕管我叫大狗熊,只要让我吃香喝辣那也无所谓。眼见着粮食没了,妈妈好像会变戏法,今天给我们做高粱面汤,明天给我们贴小米干粮,再后天让我们吃一顿杂合面的蒸饺子。我觉得妈妈一定是神仙转世,在弹尽粮绝的关键时刻,会像神仙似得能点石成金。我怀着好奇心,躲在旮旯里看看妈妈如何化腐朽此为神奇。快做中午饭的时候,妈妈拿了木升不慌不忙的走进了草屋子,在开草屋门的时候,紧张的看了又看,确定没有异常之后,钻进草屋子,过了好一会才出来。我趁妈妈不注意,钻进草屋子,在一堆秫秸后面,发现了两个大缸,一个缸是玉米面,一个缸是小米。我兴高采烈的跑到妈妈跟前,说出我看到的秘密。妈妈顿时把脸拉了下来,非常严肃的说“你不能出去瞎咧咧,小心我扯你嘴巴。”我怕妈妈打我嘴巴,把看到的秘密烂到肚子里。
妈妈勤快是出了名的,邻居们大娘婶子们夸奖我妈妈“嘴一分,手一分。”刚开春的时候,妈妈拿着镰刀到山上、沟崖处,一筐筐掳榆钱,回到家里仔仔细细把虫子和残品挑出去,用干净水洗了,用玉米面和了,放上葱花、咸盐、荤油给我们做榆钱干粮。我最喜欢吃榆钱干粮,有时候比大人都能吃。放学后,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掀开锅盖,拿着榆钱干粮跟伙伴们炫耀。每个人自然都分到一小块榆钱干粮,我成了大家拥戴的领袖,拉帮结派,哄哄嚷嚷到处滋事。每次在野外开战,我带着我的兵将把人打哭,大人领着孩子,跟我妈急头白脸理论。我妈总是满脸憨笑,掀开过拿出榆钱干粮,让人家尝新鲜。一场场异常激烈的矛盾,在妈妈的微笑和榆钱干粮的互换中得到平息。
妈妈在春天除了用榆钱做干粮,还会用榆钱做面汤。妈妈过日子仔细,她经常给爸爸上课“过日子,不能有米一锅,有柴一灶,要细水长流,掐算着过日子。”妈妈烧开一锅开水,灌满暖壶就便将和好的面蛋,均匀的洒向花花翻开的锅里,在均匀的洒满榆钱。妈妈,很娴熟的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往下做,一大面盆面汤,三下五除二就非常轻松的做好了。榆钱面汤吃到嘴里,感觉滑滑,特别香甜。邻邻居居的婶子叔叔,闻见榆钱面汤的味道,便找一个借口,笑嘻嘻串门。妈妈总是热情的给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汤,婶子叔叔先拿捏一番,妈妈便说“过门槛吃一碗,你客气啥,要是再扭扭捏捏,拿腔摆怪,就不许你们叫我嫂子。”来人便仗义的端起碗,秃噜秃噜吃一碗,吃得真是舔嘴咋舌。妈妈也不再让,来人走后,自言自语说“给你一碗尝尝,那也就是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一张脸,我可不能管饱。我家的粮食也不够吃。”
槐树花开会有一股股甜丝丝的香气,从山坳沟壑里飘到房前屋后。妈妈在队里干活无论有多忙,一筐一筐往家挎槐树花。槐树的枝杈长满了尖尖的刺刺,稍不留神,就会把衣服挂出个大口子,手心手背被划得鲜血淋淋。妈妈不畏其难,一天中午挎回一筐子。妈妈的脸划破了皮,手也流血,便哭着对妈妈说“妈,你别掳刺槐花了,脸都刺破了,手也弄流血了,那多疼呀。”妈妈满不在乎“傻小子,你哭唧唧的干啥。干活吗,蹭块皮,划破肉,那都是正常。傻小子,你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吧,妈妈这点小屁伤,离心大老远,一顶点事都没有。”......我最喜欢看,妈妈做槐花蒸饺了。先把白白的槐花,倒在笸箩里,一点点摘,除去杂物,包括虫子,小棍子,被虫子咬残的花瓣。然后把槐花倒在一个黑色的瓦盆里,浇上井凉水,用长把勺子,反反复复搅动,再捞出来沥水。妈妈点着柴火,我坐在灶前的蒲团上,咕咕哒哒拉风匣。快开锅时,妈妈将槐花倒进锅里,来回折个,然后再捞出来,用笼布裹住槐花,放在菜板上,双手用力压揉,水顺着笼布哗哗的往下流......妈妈把槐花蒸饺,热气腾腾的端上饭桌时,妈妈嘴角上挂着笑。她看着我,一口接一口吃槐花蒸饺时,总是鼓励我“多吃几个,再多吃几个,长一个大个,身大力不亏。”如今,我已经有些年头没吃槐花饺子,今天春天我老婆特意从老家掳了槐花,给我做一顿槐花饺子,各种作料齐全,却再也找不到当年那种感觉了。
在粮食稀缺的年月,什么东西都可以入口。我家的房上有块山地,种庄稼不长,于是就种了紫花苜蓿。刚种完地,嫩嫩的苜蓿芽便闹哄哄的长出来。这些苜蓿芽成了人们充饥解饿的好东西。左邻右舍的嫂子婶子们,利用黑天的时候,拉帮结伙到苜蓿地挖苜蓿芽。队里为了保护革命的胜利果实,就派杜绝户看苜蓿。他无儿无女,大公无私,属于秃子楞瞎子狠的那类人。每天总能抓住几个偷苜蓿的贼,杜绝户用大脚丫子,把框子踩得支零破碎,还把头苜的贼,一个不落的上报队长那里,开会批斗,扣工分。我妈妈也去挖苜蓿芽子,但是跑单帮。那年,我跟妈妈作伴挖苜蓿芽子,不料被杜绝户逮住。他看了我们一眼,放低声音说“挖满一筐子赶紧走。”杜绝户说完转身就走。在饭桌上吃苜蓿芽子玉米饼子,我挑头说起我们被杜绝户抓的事情,妈妈满脸通红。爸爸很生气,跟妈妈拍桌子,爸爸是队委会成员,必须给革命群众起带头作用“你就那么馋,馋就拿鞋底子往嘴巴子上打几下。”妈妈不言语,平静的吃饭。这事没几天,杜绝户就拎着大包小包被子棉衣服让妈妈拆洗。爸爸就妈妈偷挖苜蓿芽子事件,狠“斗”杜绝户私字一闪念,嘚嘚咕咕说了一大堆革命话。杜绝户却挠挠脑袋辩护“现在家家户户都不够吃,偷苜蓿那是没办法的事儿。只要是不成群结伙去偷,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妈妈挖苜蓿总喜欢拉单帮,原来她摸透了杜绝户的心理了。若干年后,我猛然想到,我妈妈年年免费为杜绝户做棉衣服拆洗被褥,那是再还欠情呀。
耪地的时候,家里粮食就见底了。妈妈非常淡定,不着急不上火,在人们歇息的时候,她挖猪毛菜掳树叶,回到家摘了根须,洗去泥土,拌了玉米面做干粮饼子吃,菜多粮食少,但是妈妈会调配,酱油、荤油、花椒、大料佐料放全,咸淡合适,格外的好吃。妈妈在家里偷着养了五只大母鸡,每天至少都能捡到三个鸡蛋,中午饭总能吃到一盘韭菜炒鸡蛋。我记得特别清楚,妈妈在端炒鸡蛋前,好像做贼一样,前后左右看一个遍,门轻轻的插上,再轻手轻脚把鸡蛋端上来。我很傻,总要高兴的喊叫,妈妈总训斥我,说我狗肚子盛不了三两荤油。我却不长记性,一看到金黄色炒鸡蛋,兴奋地用筷子当当敲碗,要做欢呼状,妈妈用手指点我鼻子,小声而严厉的训斥“你再喊,把鬼招来,让你饿肚子。”在妈妈的眼里,闻着香气,敲门而进我的那些伙伴们,统称为馋鬼。妈妈骂我是调皮鬼、捣蛋鬼、傻鬼。在她有限的语汇里,鬼不是贬义词,相对来说应该有褒奖的成分。我在妈妈的警告下不再闹腾了,手里拿着菜饼子,就着喷香的炒鸡蛋,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我发现,爸、妈、姐吃鸡蛋,都是吃一小点点,几乎全用咸菜下饭,那盘炒鸡蛋几乎全让我吃了。妈妈看着我吃饭的样子,嘴角上挂着笑,总在说“好小子,多吃点,好长大个,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你。”
妈妈年年都喜欢在自留地带豆角,拔苗耪地费事费工,爸爸埋怨妈妈如何如何,他却笑而不答,却年年在自留地带豆角。农历六月以后,几场倾盆大雨过后,玉米便咔咔拔节旺长。豆角子也跟着长。妈妈看地回来说,“咱家的豆角子开花了,紫色的小花一嘟噜一串的,带这些豆角子肯定能够全家吃。”全家人都沉浸在美妙的期待之中,豆角子不但当菜吃,最主要的还能当饭扛饿。十多天后,妈妈天天贪黑挎回一大柳编筐豆角。一向矜持寡言的爸爸,紧锁的眉头也顿时舒展开来。他坐在桃树下,主动承担了摘豆角的义务。早晨我还没起被窝,那股浓郁的香气,就顺着门缝钻进来。我顿时睡意全无,洗手洗脸,当妈妈的跟屁虫,嘟囔着要吃豆角。饭少我们就以豆角为主,一大铝盆豆角,被全部吃光。每次炖豆角,妈妈总在豆角里放几块腊肉,这腊肉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为我嘴里的美食。我那时真是一个得一望二不知足的人。我反复的说“妈妈。我要肉肉,要肉肉。”爸爸心烦了,筷子当当的敲着碗,狠狠的说“下次炖豆角,一块都不放,这孩子让你惯的一点人样都没有。”妈妈不接爸爸话茬,总是给我许愿。那天上集给我卖大麻花,买一大把糖块.....过了立秋,豆角就吃不过来了。豆角的豆子格外饱满,妈妈偏心眼,每次都特意给我留一碗豆子特别的好吃,直到现在我保留着吃豆角豆子的习惯。
立秋过后,总算看到了希望。虽然年景不好,如干旱、雹灾、虫灾等等,都在消减着收成。爸爸蔫头耷脑,为工分不值钱犯愁,为完不成公粮任务愁,为家里这些张嘴吃饭犯愁。妈妈却是一个典型的乐天派,不知道啥叫犯愁。妈妈跟我说再过几天,就可以吃烤玉米。妈妈这话说完还没过五天,妈妈就把嫩玉米掰回来,用铁筷子穿上,放在火上烤。妈妈既要往锅里贴玉米饼子,还要照看灶间的玉米别烤糊了,经常进行转动。饭做熟了,玉米也烤好了。烤玉米金黄色,一个玉米粒都不焦糊,亮晶晶的好像一粒粒珍珠。我在拿着烤玉米在大门外显摆着吃时,总会招来一片赞叹声“小子,你妈可真巧,看看这玉米烤的真好。能不能给二娘吃一口。”我总是把玉米藏在背后,大声喊“这是我妈妈给我烤的,就是不给你吃,把你大牙馋掉。”说完,就赶紧往院里跑。二娘不追我,笑嘻嘻看着我“这臭小子,真嘎真嘎。”......如今,行走在繁花的街市上,也有烤玉米,也给女儿买过,但是吃着远不如妈妈给烤的香。
自留地的黄豆鼓豆后,也正是玉米成熟的时候。妈妈总是起早到自留地把玉米棒掰下,用化肥袋子扛回来。我们吃早饭,妈妈就咔咔的把玉米棒扒得干干净净。妈妈冲我笑笑,好像变魔术似的,从化肥袋子里面掏出一堆绿豆夹。“儿子,这是啥。”我顿时兴奋起来,饭也不吃了,哧溜一下从炕沿溜下来“妈妈,毛豆。我要吃毛豆。”爸爸怪起妈妈来“你呀,竟干烧香惹鬼的买卖,瞧瞧这孩子饭也不好好吃。这孩子让你惯下去,非瞎长不可。”妈妈不在乎爸爸的埋怨,用手在我脸蛋上摸摸“傻儿子,赶紧好好吃饭。你瞧瞧这脸蛋瘦的好像皮包骨,再不好好吃饭,二妮就不给你当媳妇了。”二妮比我小七个月,张家婶子给我许过愿,二妮长大之后,就给我当媳妇。我听了这话,马上回到炕上,把一碗饭吃得精光,比小猫舔得都干净。我举着碗给妈妈看“妈妈,我吃完了。”妈妈紧紧抱住我,在脸上响亮的亲一口“我大儿子真有出息。”
中午妈妈便给我们端上热乎乎的玉米棒、一盖帘毛毛豆。妈妈把毛毛豆给姐姐和我分开,我那份舍不得吃。妈妈睁大眼睛看着我“儿子,毛毛豆咋不吃。”我笑了,很可爱“妈,这毛毛豆给我媳妇吃。”妈妈笑了,笑得直不起腰。姐姐用手拨弄两个脸蛋“不要脸,小流氓。”我委屈的哭了,妈妈把我搂在怀里掉眼泪,她假装追姐姐给我出气,姐姐跑出了家门,我便破涕为笑,忘记了所有的事情,把我的那份毛毛豆吃得干干净净.....
在饥荒的童年里,因为妈妈的勤劳睿智,让我逃过了饥饿,对吃不饱穿不暖,没有任何印象。日子好起来之后,妈妈特别节俭,每年都要储备粮食,她是被饿怕了,看着囤满仓流的粮食,她总是笑了,反反复复说“仓里有粮,心里不慌。”我结婚后,有了孩子。妈妈对孩子要求很严,当孩子剩饭时,妈妈总是严肃的说“孩子,别剩饭呀,剩饭找对象找一个麻子蛋儿。”千方百计让孩子把饭吃掉,孩子实在不吃,她就端起剩饭吃得干干净净“好年月想着赖年月,粮食是好东西,糟蹋粮食有罪呀。”妈妈不会说大道理,她经历过饥荒岁月,总是在现身说法。如今,我也养成了好习惯,就是在单位吃饭,从不剩饭剩菜,顿顿都是连菜汤也不剩。我想,虽然饥荒岁月已经离开我们好长时间,但是不浪费要勤俭对我们还是挺实用的。我小时候,大多数人家都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困顿生活。我家里的日子也是异常的紧巴,妈妈做饭算计着做,早晨做啥饭,中午做啥饭,晚上做啥饭,一顿饭下多少米面,用称量着做。妈妈会打理能算计,细水长流,在饥荒岁月里,我没有像其他人家的孩子,被饿得面黄肌瘦,排便困难被憋的嗷嗷叫唤……至今回想起来,很多事情,在脑海里生动呈现,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神使鬼差的促使我,写下这一段饥荒岁月零零碎碎的记忆。
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成了重点保护对象,姐姐嘲笑我是大熊猫。我不在意这不雅的外号,哪怕管我叫大狗熊,只要让我吃香喝辣那也无所谓。眼见着粮食没了,妈妈好像会变戏法,今天给我们做高粱面汤,明天给我们贴小米干粮,再后天让我们吃一顿杂合面的蒸饺子。我觉得妈妈一定是神仙转世,在弹尽粮绝的关键时刻,会像神仙似得能点石成金。我怀着好奇心,躲在旮旯里看看妈妈如何化腐朽此为神奇。快做中午饭的时候,妈妈拿了木升不慌不忙的走进了草屋子,在开草屋门的时候,紧张的看了又看,确定没有异常之后,钻进草屋子,过了好一会才出来。我趁妈妈不注意,钻进草屋子,在一堆秫秸后面,发现了两个大缸,一个缸是玉米面,一个缸是小米。我兴高采烈的跑到妈妈跟前,说出我看到的秘密。妈妈顿时把脸拉了下来,非常严肃的说“你不能出去瞎咧咧,小心我扯你嘴巴。”我怕妈妈打我嘴巴,把看到的秘密烂到肚子里。
妈妈勤快是出了名的,邻居们大娘婶子们夸奖我妈妈“嘴一分,手一分。”刚开春的时候,妈妈拿着镰刀到山上、沟崖处,一筐筐掳榆钱,回到家里仔仔细细把虫子和残品挑出去,用干净水洗了,用玉米面和了,放上葱花、咸盐、荤油给我们做榆钱干粮。我最喜欢吃榆钱干粮,有时候比大人都能吃。放学后,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掀开锅盖,拿着榆钱干粮跟伙伴们炫耀。每个人自然都分到一小块榆钱干粮,我成了大家拥戴的领袖,拉帮结派,哄哄嚷嚷到处滋事。每次在野外开战,我带着我的兵将把人打哭,大人领着孩子,跟我妈急头白脸理论。我妈总是满脸憨笑,掀开过拿出榆钱干粮,让人家尝新鲜。一场场异常激烈的矛盾,在妈妈的微笑和榆钱干粮的互换中得到平息。
妈妈在春天除了用榆钱做干粮,还会用榆钱做面汤。妈妈过日子仔细,她经常给爸爸上课“过日子,不能有米一锅,有柴一灶,要细水长流,掐算着过日子。”妈妈烧开一锅开水,灌满暖壶就便将和好的面蛋,均匀的洒向花花翻开的锅里,在均匀的洒满榆钱。妈妈,很娴熟的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往下做,一大面盆面汤,三下五除二就非常轻松的做好了。榆钱面汤吃到嘴里,感觉滑滑,特别香甜。邻邻居居的婶子叔叔,闻见榆钱面汤的味道,便找一个借口,笑嘻嘻串门。妈妈总是热情的给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汤,婶子叔叔先拿捏一番,妈妈便说“过门槛吃一碗,你客气啥,要是再扭扭捏捏,拿腔摆怪,就不许你们叫我嫂子。”来人便仗义的端起碗,秃噜秃噜吃一碗,吃得真是舔嘴咋舌。妈妈也不再让,来人走后,自言自语说“给你一碗尝尝,那也就是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一张脸,我可不能管饱。我家的粮食也不够吃。”
槐树花开会有一股股甜丝丝的香气,从山坳沟壑里飘到房前屋后。妈妈在队里干活无论有多忙,一筐一筐往家挎槐树花。槐树的枝杈长满了尖尖的刺刺,稍不留神,就会把衣服挂出个大口子,手心手背被划得鲜血淋淋。妈妈不畏其难,一天中午挎回一筐子。妈妈的脸划破了皮,手也流血,便哭着对妈妈说“妈,你别掳刺槐花了,脸都刺破了,手也弄流血了,那多疼呀。”妈妈满不在乎“傻小子,你哭唧唧的干啥。干活吗,蹭块皮,划破肉,那都是正常。傻小子,你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吧,妈妈这点小屁伤,离心大老远,一顶点事都没有。”......我最喜欢看,妈妈做槐花蒸饺了。先把白白的槐花,倒在笸箩里,一点点摘,除去杂物,包括虫子,小棍子,被虫子咬残的花瓣。然后把槐花倒在一个黑色的瓦盆里,浇上井凉水,用长把勺子,反反复复搅动,再捞出来沥水。妈妈点着柴火,我坐在灶前的蒲团上,咕咕哒哒拉风匣。快开锅时,妈妈将槐花倒进锅里,来回折个,然后再捞出来,用笼布裹住槐花,放在菜板上,双手用力压揉,水顺着笼布哗哗的往下流......妈妈把槐花蒸饺,热气腾腾的端上饭桌时,妈妈嘴角上挂着笑。她看着我,一口接一口吃槐花蒸饺时,总是鼓励我“多吃几个,再多吃几个,长一个大个,身大力不亏。”如今,我已经有些年头没吃槐花饺子,今天春天我老婆特意从老家掳了槐花,给我做一顿槐花饺子,各种作料齐全,却再也找不到当年那种感觉了。
在粮食稀缺的年月,什么东西都可以入口。我家的房上有块山地,种庄稼不长,于是就种了紫花苜蓿。刚种完地,嫩嫩的苜蓿芽便闹哄哄的长出来。这些苜蓿芽成了人们充饥解饿的好东西。左邻右舍的嫂子婶子们,利用黑天的时候,拉帮结伙到苜蓿地挖苜蓿芽。队里为了保护革命的胜利果实,就派杜绝户看苜蓿。他无儿无女,大公无私,属于秃子楞瞎子狠的那类人。每天总能抓住几个偷苜蓿的贼,杜绝户用大脚丫子,把框子踩得支零破碎,还把头苜的贼,一个不落的上报队长那里,开会批斗,扣工分。我妈妈也去挖苜蓿芽子,但是跑单帮。那年,我跟妈妈作伴挖苜蓿芽子,不料被杜绝户逮住。他看了我们一眼,放低声音说“挖满一筐子赶紧走。”杜绝户说完转身就走。在饭桌上吃苜蓿芽子玉米饼子,我挑头说起我们被杜绝户抓的事情,妈妈满脸通红。爸爸很生气,跟妈妈拍桌子,爸爸是队委会成员,必须给革命群众起带头作用“你就那么馋,馋就拿鞋底子往嘴巴子上打几下。”妈妈不言语,平静的吃饭。这事没几天,杜绝户就拎着大包小包被子棉衣服让妈妈拆洗。爸爸就妈妈偷挖苜蓿芽子事件,狠“斗”杜绝户私字一闪念,嘚嘚咕咕说了一大堆革命话。杜绝户却挠挠脑袋辩护“现在家家户户都不够吃,偷苜蓿那是没办法的事儿。只要是不成群结伙去偷,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妈妈挖苜蓿总喜欢拉单帮,原来她摸透了杜绝户的心理了。若干年后,我猛然想到,我妈妈年年免费为杜绝户做棉衣服拆洗被褥,那是再还欠情呀。
耪地的时候,家里粮食就见底了。妈妈非常淡定,不着急不上火,在人们歇息的时候,她挖猪毛菜掳树叶,回到家摘了根须,洗去泥土,拌了玉米面做干粮饼子吃,菜多粮食少,但是妈妈会调配,酱油、荤油、花椒、大料佐料放全,咸淡合适,格外的好吃。妈妈在家里偷着养了五只大母鸡,每天至少都能捡到三个鸡蛋,中午饭总能吃到一盘韭菜炒鸡蛋。我记得特别清楚,妈妈在端炒鸡蛋前,好像做贼一样,前后左右看一个遍,门轻轻的插上,再轻手轻脚把鸡蛋端上来。我很傻,总要高兴的喊叫,妈妈总训斥我,说我狗肚子盛不了三两荤油。我却不长记性,一看到金黄色炒鸡蛋,兴奋地用筷子当当敲碗,要做欢呼状,妈妈用手指点我鼻子,小声而严厉的训斥“你再喊,把鬼招来,让你饿肚子。”在妈妈的眼里,闻着香气,敲门而进我的那些伙伴们,统称为馋鬼。妈妈骂我是调皮鬼、捣蛋鬼、傻鬼。在她有限的语汇里,鬼不是贬义词,相对来说应该有褒奖的成分。我在妈妈的警告下不再闹腾了,手里拿着菜饼子,就着喷香的炒鸡蛋,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我发现,爸、妈、姐吃鸡蛋,都是吃一小点点,几乎全用咸菜下饭,那盘炒鸡蛋几乎全让我吃了。妈妈看着我吃饭的样子,嘴角上挂着笑,总在说“好小子,多吃点,好长大个,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你。”
妈妈年年都喜欢在自留地带豆角,拔苗耪地费事费工,爸爸埋怨妈妈如何如何,他却笑而不答,却年年在自留地带豆角。农历六月以后,几场倾盆大雨过后,玉米便咔咔拔节旺长。豆角子也跟着长。妈妈看地回来说,“咱家的豆角子开花了,紫色的小花一嘟噜一串的,带这些豆角子肯定能够全家吃。”全家人都沉浸在美妙的期待之中,豆角子不但当菜吃,最主要的还能当饭扛饿。十多天后,妈妈天天贪黑挎回一大柳编筐豆角。一向矜持寡言的爸爸,紧锁的眉头也顿时舒展开来。他坐在桃树下,主动承担了摘豆角的义务。早晨我还没起被窝,那股浓郁的香气,就顺着门缝钻进来。我顿时睡意全无,洗手洗脸,当妈妈的跟屁虫,嘟囔着要吃豆角。饭少我们就以豆角为主,一大铝盆豆角,被全部吃光。每次炖豆角,妈妈总在豆角里放几块腊肉,这腊肉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为我嘴里的美食。我那时真是一个得一望二不知足的人。我反复的说“妈妈。我要肉肉,要肉肉。”爸爸心烦了,筷子当当的敲着碗,狠狠的说“下次炖豆角,一块都不放,这孩子让你惯的一点人样都没有。”妈妈不接爸爸话茬,总是给我许愿。那天上集给我卖大麻花,买一大把糖块.....过了立秋,豆角就吃不过来了。豆角的豆子格外饱满,妈妈偏心眼,每次都特意给我留一碗豆子特别的好吃,直到现在我保留着吃豆角豆子的习惯。
立秋过后,总算看到了希望。虽然年景不好,如干旱、雹灾、虫灾等等,都在消减着收成。爸爸蔫头耷脑,为工分不值钱犯愁,为完不成公粮任务愁,为家里这些张嘴吃饭犯愁。妈妈却是一个典型的乐天派,不知道啥叫犯愁。妈妈跟我说再过几天,就可以吃烤玉米。妈妈这话说完还没过五天,妈妈就把嫩玉米掰回来,用铁筷子穿上,放在火上烤。妈妈既要往锅里贴玉米饼子,还要照看灶间的玉米别烤糊了,经常进行转动。饭做熟了,玉米也烤好了。烤玉米金黄色,一个玉米粒都不焦糊,亮晶晶的好像一粒粒珍珠。我在拿着烤玉米在大门外显摆着吃时,总会招来一片赞叹声“小子,你妈可真巧,看看这玉米烤的真好。能不能给二娘吃一口。”我总是把玉米藏在背后,大声喊“这是我妈妈给我烤的,就是不给你吃,把你大牙馋掉。”说完,就赶紧往院里跑。二娘不追我,笑嘻嘻看着我“这臭小子,真嘎真嘎。”......如今,行走在繁花的街市上,也有烤玉米,也给女儿买过,但是吃着远不如妈妈给烤的香。
自留地的黄豆鼓豆后,也正是玉米成熟的时候。妈妈总是起早到自留地把玉米棒掰下,用化肥袋子扛回来。我们吃早饭,妈妈就咔咔的把玉米棒扒得干干净净。妈妈冲我笑笑,好像变魔术似的,从化肥袋子里面掏出一堆绿豆夹。“儿子,这是啥。”我顿时兴奋起来,饭也不吃了,哧溜一下从炕沿溜下来“妈妈,毛豆。我要吃毛豆。”爸爸怪起妈妈来“你呀,竟干烧香惹鬼的买卖,瞧瞧这孩子饭也不好好吃。这孩子让你惯下去,非瞎长不可。”妈妈不在乎爸爸的埋怨,用手在我脸蛋上摸摸“傻儿子,赶紧好好吃饭。你瞧瞧这脸蛋瘦的好像皮包骨,再不好好吃饭,二妮就不给你当媳妇了。”二妮比我小七个月,张家婶子给我许过愿,二妮长大之后,就给我当媳妇。我听了这话,马上回到炕上,把一碗饭吃得精光,比小猫舔得都干净。我举着碗给妈妈看“妈妈,我吃完了。”妈妈紧紧抱住我,在脸上响亮的亲一口“我大儿子真有出息。”
中午妈妈便给我们端上热乎乎的玉米棒、一盖帘毛毛豆。妈妈把毛毛豆给姐姐和我分开,我那份舍不得吃。妈妈睁大眼睛看着我“儿子,毛毛豆咋不吃。”我笑了,很可爱“妈,这毛毛豆给我媳妇吃。”妈妈笑了,笑得直不起腰。姐姐用手拨弄两个脸蛋“不要脸,小流氓。”我委屈的哭了,妈妈把我搂在怀里掉眼泪,她假装追姐姐给我出气,姐姐跑出了家门,我便破涕为笑,忘记了所有的事情,把我的那份毛毛豆吃得干干净净.....
在饥荒的童年里,因为妈妈的勤劳睿智,让我逃过了饥饿,对吃不饱穿不暖,没有任何印象。日子好起来之后,妈妈特别节俭,每年都要储备粮食,她是被饿怕了,看着囤满仓流的粮食,她总是笑了,反反复复说“仓里有粮,心里不慌。”我结婚后,有了孩子。妈妈对孩子要求很严,当孩子剩饭时,妈妈总是严肃的说“孩子,别剩饭呀,剩饭找对象找一个麻子蛋儿。”千方百计让孩子把饭吃掉,孩子实在不吃,她就端起剩饭吃得干干净净“好年月想着赖年月,粮食是好东西,糟蹋粮食有罪呀。”妈妈不会说大道理,她经历过饥荒岁月,总是在现身说法。如今,我也养成了好习惯,就是在单位吃饭,从不剩饭剩菜,顿顿都是连菜汤也不剩。我想,虽然饥荒岁月已经离开我们好长时间,但是不浪费要勤俭对我们还是挺实用的。我小时候,大多数人家都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困顿生活。我家里的日子也是异常的紧巴,妈妈做饭算计着做,早晨做啥饭,中午做啥饭,晚上做啥饭,一顿饭下多少米面,用称量着做。妈妈会打理能算计,细水长流,在饥荒岁月里,我没有像其他人家的孩子,被饿得面黄肌瘦,排便困难被憋的嗷嗷叫唤……至今回想起来,很多事情,在脑海里生动呈现,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神使鬼差的促使我,写下这一段饥荒岁月零零碎碎的记忆。
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成了重点保护对象,姐姐嘲笑我是大熊猫。我不在意这不雅的外号,哪怕管我叫大狗熊,只要让我吃香喝辣那也无所谓。眼见着粮食没了,妈妈好像会变戏法,今天给我们做高粱面汤,明天给我们贴小米干粮,再后天让我们吃一顿杂合面的蒸饺子。我觉得妈妈一定是神仙转世,在弹尽粮绝的关键时刻,会像神仙似得能点石成金。我怀着好奇心,躲在旮旯里看看妈妈如何化腐朽此为神奇。快做中午饭的时候,妈妈拿了木升不慌不忙的走进了草屋子,在开草屋门的时候,紧张的看了又看,确定没有异常之后,钻进草屋子,过了好一会才出来。我趁妈妈不注意,钻进草屋子,在一堆秫秸后面,发现了两个大缸,一个缸是玉米面,一个缸是小米。我兴高采烈的跑到妈妈跟前,说出我看到的秘密。妈妈顿时把脸拉了下来,非常严肃的说“你不能出去瞎咧咧,小心我扯你嘴巴。”我怕妈妈打我嘴巴,把看到的秘密烂到肚子里。
妈妈勤快是出了名的,邻居们大娘婶子们夸奖我妈妈“嘴一分,手一分。”刚开春的时候,妈妈拿着镰刀到山上、沟崖处,一筐筐掳榆钱,回到家里仔仔细细把虫子和残品挑出去,用干净水洗了,用玉米面和了,放上葱花、咸盐、荤油给我们做榆钱干粮。我最喜欢吃榆钱干粮,有时候比大人都能吃。放学后,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掀开锅盖,拿着榆钱干粮跟伙伴们炫耀。每个人自然都分到一小块榆钱干粮,我成了大家拥戴的领袖,拉帮结派,哄哄嚷嚷到处滋事。每次在野外开战,我带着我的兵将把人打哭,大人领着孩子,跟我妈急头白脸理论。我妈总是满脸憨笑,掀开过拿出榆钱干粮,让人家尝新鲜。一场场异常激烈的矛盾,在妈妈的微笑和榆钱干粮的互换中得到平息。
妈妈在春天除了用榆钱做干粮,还会用榆钱做面汤。妈妈过日子仔细,她经常给爸爸上课“过日子,不能有米一锅,有柴一灶,要细水长流,掐算着过日子。”妈妈烧开一锅开水,灌满暖壶就便将和好的面蛋,均匀的洒向花花翻开的锅里,在均匀的洒满榆钱。妈妈,很娴熟的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往下做,一大面盆面汤,三下五除二就非常轻松的做好了。榆钱面汤吃到嘴里,感觉滑滑,特别香甜。邻邻居居的婶子叔叔,闻见榆钱面汤的味道,便找一个借口,笑嘻嘻串门。妈妈总是热情的给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汤,婶子叔叔先拿捏一番,妈妈便说“过门槛吃一碗,你客气啥,要是再扭扭捏捏,拿腔摆怪,就不许你们叫我嫂子。”来人便仗义的端起碗,秃噜秃噜吃一碗,吃得真是舔嘴咋舌。妈妈也不再让,来人走后,自言自语说“给你一碗尝尝,那也就是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一张脸,我可不能管饱。我家的粮食也不够吃。”
槐树花开会有一股股甜丝丝的香气,从山坳沟壑里飘到房前屋后。妈妈在队里干活无论有多忙,一筐一筐往家挎槐树花。槐树的枝杈长满了尖尖的刺刺,稍不留神,就会把衣服挂出个大口子,手心手背被划得鲜血淋淋。妈妈不畏其难,一天中午挎回一筐子。妈妈的脸划破了皮,手也流血,便哭着对妈妈说“妈,你别掳刺槐花了,脸都刺破了,手也弄流血了,那多疼呀。”妈妈满不在乎“傻小子,你哭唧唧的干啥。干活吗,蹭块皮,划破肉,那都是正常。傻小子,你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吧,妈妈这点小屁